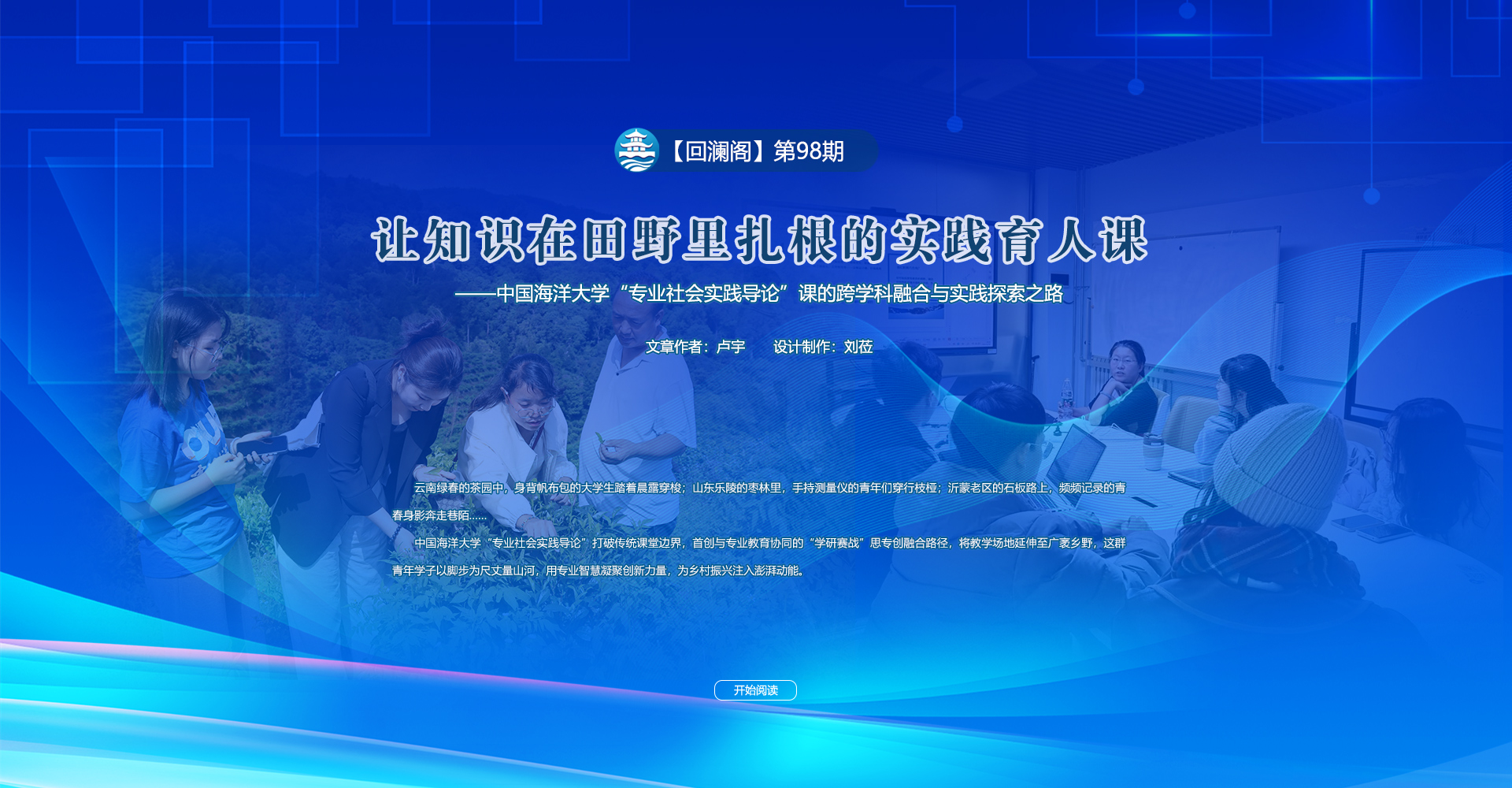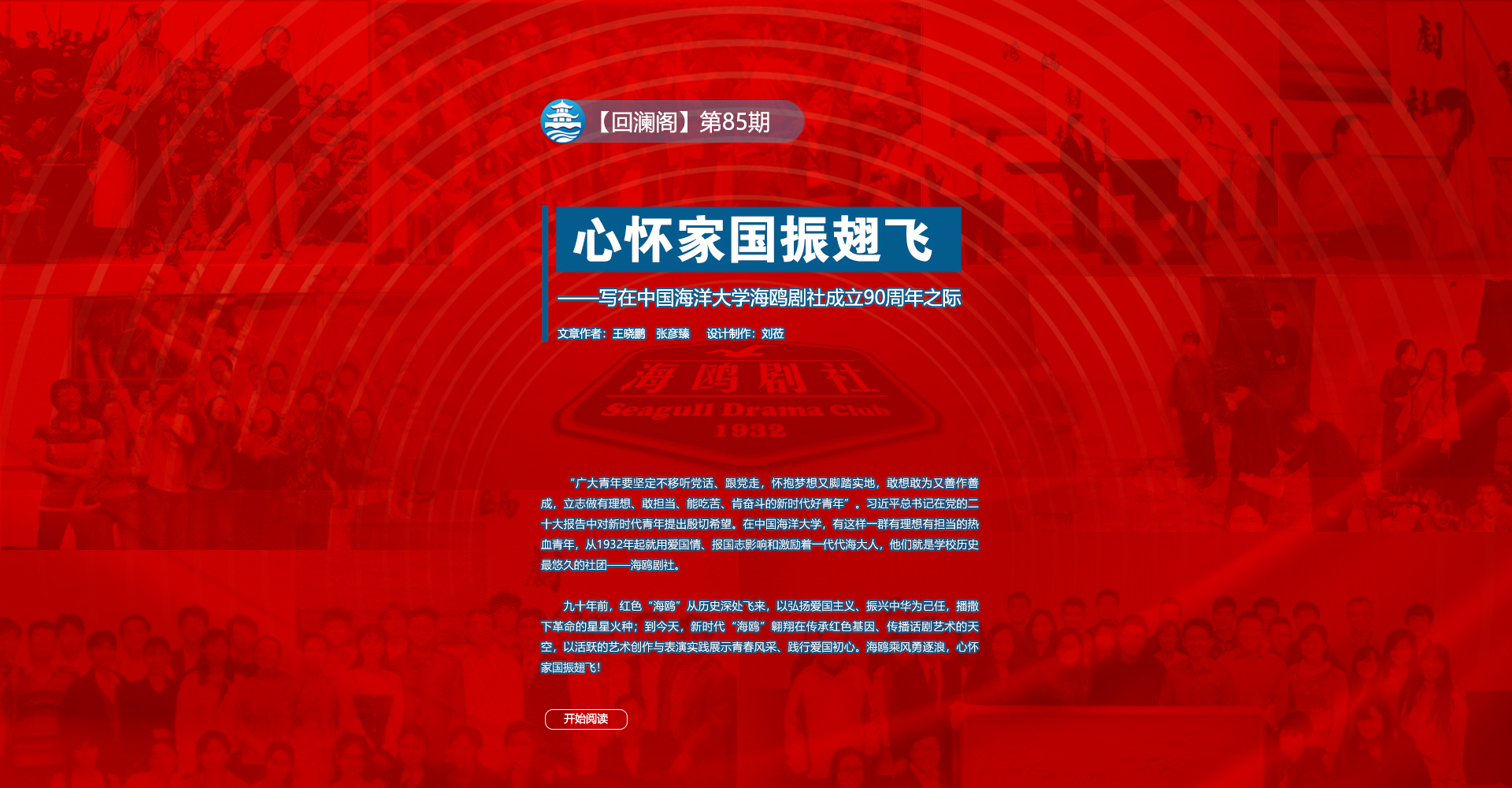奄奄一息
本站讯 12月7日晚,由校团委主办、海鸥剧社承办的话剧《安魂曲》在鱼山校区逸夫馆多功能厅上演。
该话剧以剧作家汉诺赫·列文的同名剧本为原型,根据契诃夫三部小说《洛希尔的提琴》《苦恼》和《在峡谷里》改编而成。本话剧讲述三个关于死亡的故事:一个死了儿子的马车夫,欲诉悲苦,但只能和自己的瘦马倾诉;老工匠与老妇生活五十余年,却从未给予她温暖,而是不断抱怨生活,直到她风烛残年之时,她的眼底不再温怯,而是古怪倔强,老匠人才意识到自己的悲凉;一桶沸水浇在一个婴儿身上,年轻的母亲抱着襁褓中的婴儿求医,也未能挽救一个鲜活的生命。
悲伤的亲人们在回忆与幻想中寻找温暖,周而复始地去寻找幸福的生活。
这里没有轰轰烈烈、跌宕起伏的悲欢离合,只有小人物的琐碎往事,家长里短。生离死别成为每个人必须面对的考验,但是那悲伤,只能自己默默吞咽。然而,人们仍然执着地在寻找希望的路上......
忙碌一生,却忽略爱与被爱
八堡卡子小镇,夜色寂静。小屋里的油灯发出微弱的灯光闪闪烁烁,仿佛是要被黑夜给吞没。老工匠的手指利索地打着算盘,嘴里抱怨着生活琐事:
“镇上住着一些老人,却没有几个要死的,小气巴拉的,让人不耐烦。在这儿,他们就像杂草一样攥着小命不放。”
“对于我这样造棺材的来说,生意可不好。”
“在这儿,在八堡卡子,只有贫困的生活,就一个房间的旧小屋,我,老太婆,炉子,床,几口棺材......”
一边的老人絮絮叨叨发牢骚,一旁的老妇勤勤恳恳操家务。
“老太婆,你在那儿喘什么哪!你安安静静服侍了五十几年,突然间,嗬嗬嗬,嗬嗬嗬,把我耳朵都吵聋了。老太婆,你怎么了?”老人停顿,显得不耐烦。
“喘气费劲。”老妇艰难地应着,但似乎对此感到抱歉。老人仍旧平平淡淡地问着老妇每日的家务是否都做,老妇唯唯诺诺地表示如往常一样一件事都没有落下。老人似乎心里“松了一口气”,只是不断一句“会过去的”来安抚她,“以免影响他算账”。老妇继续操劳,无法张嘴,再次粗喘气。老人此时已置之不理,专心地盘算着生活收支。
熄灯,夜已深。
老人打破沉寂,话里话外都是亏损,一句“要是我算一年的帐,那就是……一千两百块!”惊醒熟睡的老妇。此刻,老妇的喉咙里发出嘘声和尖声,脸因发烧而火红,她盯着天花板,嚅动嘴唇,脸上的表情是喜悦的,她感到自己将逃往永恒的世界,离开那个小屋,离开那些棺材,离开老人……似乎看见死亡就像看见救赎神仙一般。
“老头子,我要死了。”老妇停顿片刻,老人看着她,仿佛第一次看见。他看惯了那张脸总是苍白、恐惧、可怜的样子------但它曾经是光彩照人,充满喜悦的样子。看到老妇病危,回想她一生服侍他如此体贴入微,他开始为她端茶倒水。他要带老妇去合烙堡镇去看十九先生。

妓女攀谈
路边,天冷,哒哒的马蹄声在路面上单曲循环。马车进场,车上是一名车夫与两个妓女。老人携带着老妇坐上车。有痣妓女与有美人痣妓女攀谈着近日的“生意”。“在咱们兵马司,什么都不注意,对人不尊重。东方整个儿没落了,可是在发展中的西方,如今都是最时髦的艺术。咱们干嘛把咱这把疲累的骨头搬到石桌子去。”有美人痣妓女说道。俩妓女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巴黎------虽然她们谁也没有去过巴黎。“可我呢,一个星期前就死了儿子。”车夫悲怆地叹息,而两个妓女的话题接着延伸到卫生与消毒水,车夫继续重复“可我儿子一个礼拜以前死了,我唯一的儿子”的倾诉淹没在两个妓女歇斯底里的大笑之中。

老人抱怨
老人老妇来到十九先生家。十九先生脾气古怪,此刻他正呼呼大睡,鼾声四起。老人打断先生的睡梦,一番长篇溢美之词后,先生观望无力摊坐的老妇,诊断为流感。“六十九岁,哼,你们还想怎么样?老太太已经抽过枝发过芽了,现在瓜熟蒂落的时候到了。”先生对老妇垂危的生命不屑一顾。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呢?老人再三央求之下,“给她头上放上湿毛巾,这些药面儿每天给她两次。就这样吧。”先生敷衍着,并不再理会老人恳求。
“没空儿,伙计,没空儿,队长着呢。”也许见证太多,就会麻木,不是心硬如铁,只是无能为力。在先生眼中,流感在城里横行霸道,死亡司空见惯。
渴望被爱,压迫中走向死亡
清晨,老人老妇伫立。老妇依靠着墙,不敢躺下,担心老人谈论亏损,骂她偷懒。老人注视着老妇,拿起尺子,丈量尺寸,记在纸片上,心里盘算着:

老妇追忆往昔
“给我老婆的,棺材——六尺……半——支出还是收入?”
老妇静躺,追忆往昔------五十年前老夫妇曾有一个卷发女儿,却只有一个礼拜的生命。“从此我就把脸转向墙壁,背对这个世界。”
老妇长眠之前,睡着了,梦里有爸爸妈妈的笑,然后,他们的笑声在一瞬间停住,试图再继续一会儿,她想要那笑声继续,再继续。她知道只要在笑就好,就不会挨打,就不会挨饿,就不会发愁......
笑声,停了;天,黑了。
三个天使上场。逗乐天使胳肢老妇,快乐天使安抚老妇,悲伤天使断定老妇的死亡。众神吻老妇,“从做梦的那场小睡,我来到这场长眠, 对这场长眠我已经无话可说了。”老妇沉浸在对女儿的思念中,与世长辞。
清晨,坟茔,河岸。乌鸦尖叫着飞过,鸭群戏水。阳光强烈,波光粼粼。

故地重游
老人从坟茔地出来,听凭脚步带着他。河畔的柳树已枯黄但犹存,“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老人脑海回放记忆深处的画面------女儿,绿柳,歌声。窗外风景原来如此艳丽,而五十年来他却从未在此踱步漫游,“现在一生就过去了,没赚钱,没有乐趣,就失去了,留在我身后的只有损失,如此可怕的损失,可怕得让我发抖……为什么我一生连一次都没怜爱过我的娇妻?”
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只剩下无限的悲伤与悔恨,留给自己慢慢咀嚼。
脆弱生命,泡沫般一触即破
正当老人独自伤心之时,一位来自得禄福的不到十七岁的母亲抱着手中“熟睡”的婴儿问石桌子的路。因为遗产争端,不到半岁的婴儿就这么被残忍地用一桶开水浇灌下去。“你来不及走到石桌子去。合烙堡镇有一个十九先生。”她在老人指引下匆匆赶路求医。
“当我眼神暗淡时
请将我死去的眼睛
收进你睁开的双眼,
并将我失落的目光收进你的胸膛
请给我腾个地方,因为天冷
因为我深深眷恋你的温暖......”
哀伤凄怆的曲调,烘托台上断肠人内心的无助与焦灼。
野外的路上寒风凛冽,心急如焚的母亲怀抱着襁褓里的婴儿,她唇色发白,不顾已走一天的疲惫的双脚,自欺欺人般地安慰自己孩子还在熟睡中。到十九先生家时,已黑夜降临。
“用这些湿毛巾把他包上,到那边等着吧,那堵墙边。”十九先生的语调如往常一样。

母亲祈祷
婴儿已失去知觉,三个天使来到他身边,快乐天使讲述一个小王子的故事,婴儿停止呼吸,小小的生命转瞬即逝。
夜,很长,怎么也走不尽。苍穹月明之下,悲伤的母亲仰望星辰,寻找孩子的灵魂,内心之苦翻涌着却宣泄不出。明月啊明月,你皎洁的光,无论春天还是冬天,无论人是活着还是死亡,你一如既往。
归途,已是清晨。母亲与老人相遇故地。母亲用土埋葬小婴儿。老人欲走又止,问她是否有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从来没有,洗衣,扫地......生活带着我走,我就走......跟所有人的生活一样,先生。我站在长长的队里领我那一小把糖,队很长,我没排到。”老人触摸她的脸颊,好让她哭出来轻松些,“在一个黄昏,站在我孩子的墓前,我可以哭泣也可以沉默,我做了选择。”这或许是她唯一一次站在十字路口。

悲痛欲绝
老人远去,母亲嚎啕大哭,“生活才是谎言,这个世界才是谎言,真实的世界,是闭上眼睛的时候创造出来的,当你不能再向世界睁眼的时候,真实才在那里。”她闭眼,三个天使来到,她收到由天使翻译的来自孩子的家书。
她选择睁眼,继续坚强行走世间。
苟活悲痛,纵情玩乐何为苦
老人也病了,乘坐同一辆马车。两个醉汉嬉笑怒骂,高谈阔论着风流韵事。车夫每一句“我的儿子两个礼拜前就死了,他......”,欲倾诉的故事还未有开头,就被打断,只留下无尽的叹息:“快乐的人啊!……世界为他自己转!……”
来到十九先生家,先生仿佛是重复一遍治老妇时的话,老人意识到自己也日薄西山,“发自内心的东西,眼角的泪珠这需要条件,这是特权,不属于我们。回家去吧,我的朋友,队很长的。祝你睡个好觉。”面对老人对命运造化弄人的独白,先生吼道,也许那是洞察世间生死的麻木。
在路口,老人等着马车算了一笔账,发现从死亡中得到的只会是不错的收益:不用吃饭,不用喝水,不缴税,不会冒犯别人。生命等于损失,而死亡等于利润。“虽然这想法是正确的,可是无论如何这还是很坏的,痛苦的:为什么引导这个世界的是这么一个规则,生命只给人一次,两手空空地就过去了。”
马车载着两个妓女来,老人上车。有痣妓女与有美人痣妓女聊着日常的“玩意”,“以前,曾经有过求爱,浪漫,桂花米酒,如今呢......”醉生梦死,欢淫坦荡。在这个世界,笑就是还没哭。
妓女睡着,老人下车,马车夫沉默的内心终于山洪般喷薄爆发,“又只剩下我一个人了,痛苦离去了一会儿,又在这样的失望中回来撞击我的心灵,让我觉得我将不能忍受这些了。”在极度悲伤中想要述说,结果只能与瘦马倾诉。“教教我,我的马,教教我从现在起如何生活!……如何生活!……”

车夫倾诉
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老人在家中,追思着老妇,在美好幻象与无情现实中挣扎,遇见三个天使......
“那是同一件事情呀……对此我已经无话可说了”老人死去。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剧终谢幕。

乌鹊南飞
这是一场生与死的思考与抉择,活着,有人勤勤恳恳,却饱受生活无情的压迫;有人挥霍光阴,纸醉金迷,却无忧无虑。死亡,有人得到解脱,寻求世间未得到的幸福;有人未饱览世间人情冷暖,只能在另一个世界静静地笑,祝福着活者。活者继续苟且偷生,默默承受着对死者的悲痛,顺从生活的安排同时与生活抗争。
谢幕之后,剧组成员与台下观众合影,并在台上自我介绍,抒发内心的感受,感谢在场各位观众。观众们馈以热烈掌声。
文:黄瑜晴 图:刘昱 洪劢
编辑:黄瑜晴
责任编辑:肖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