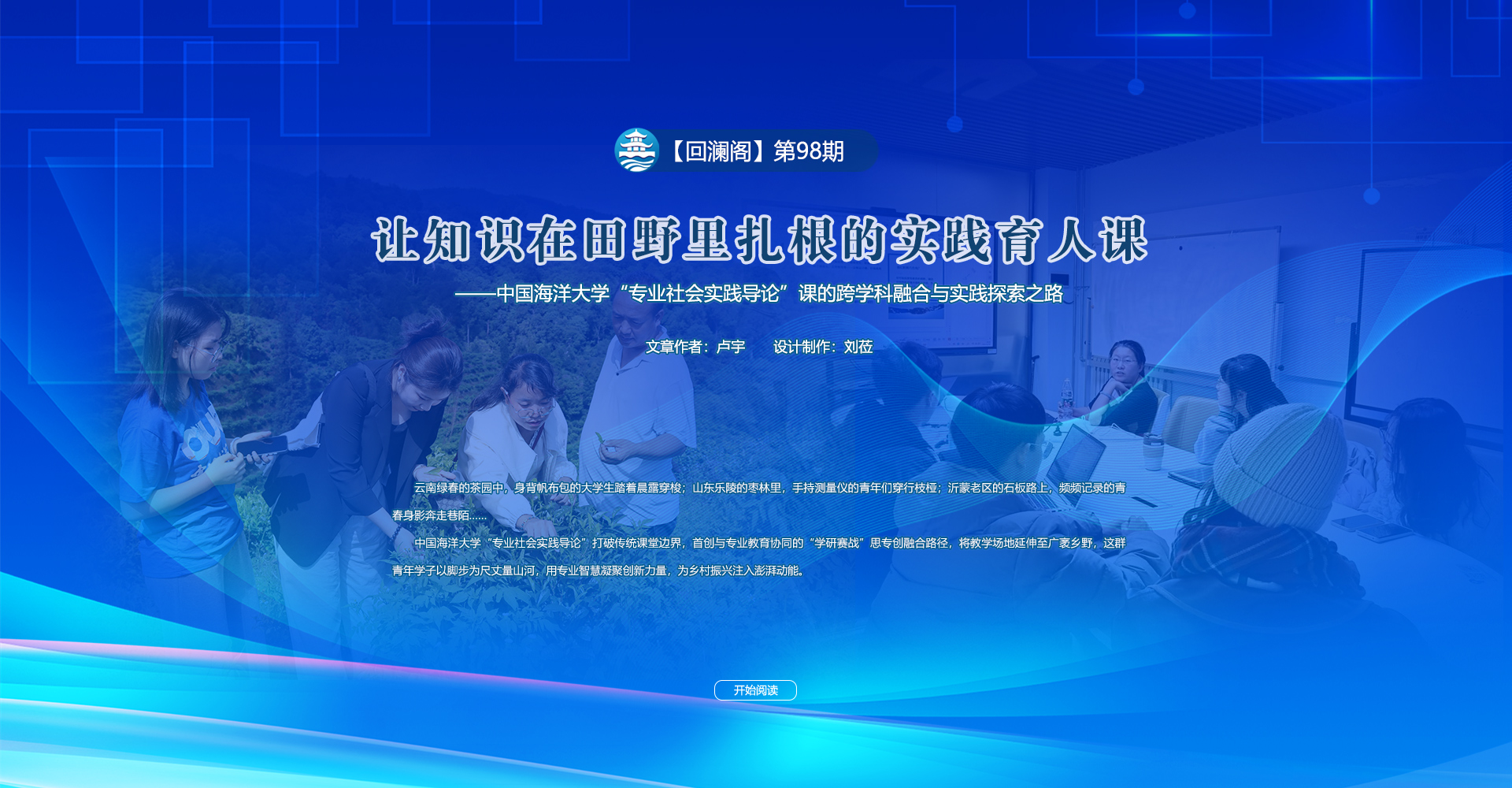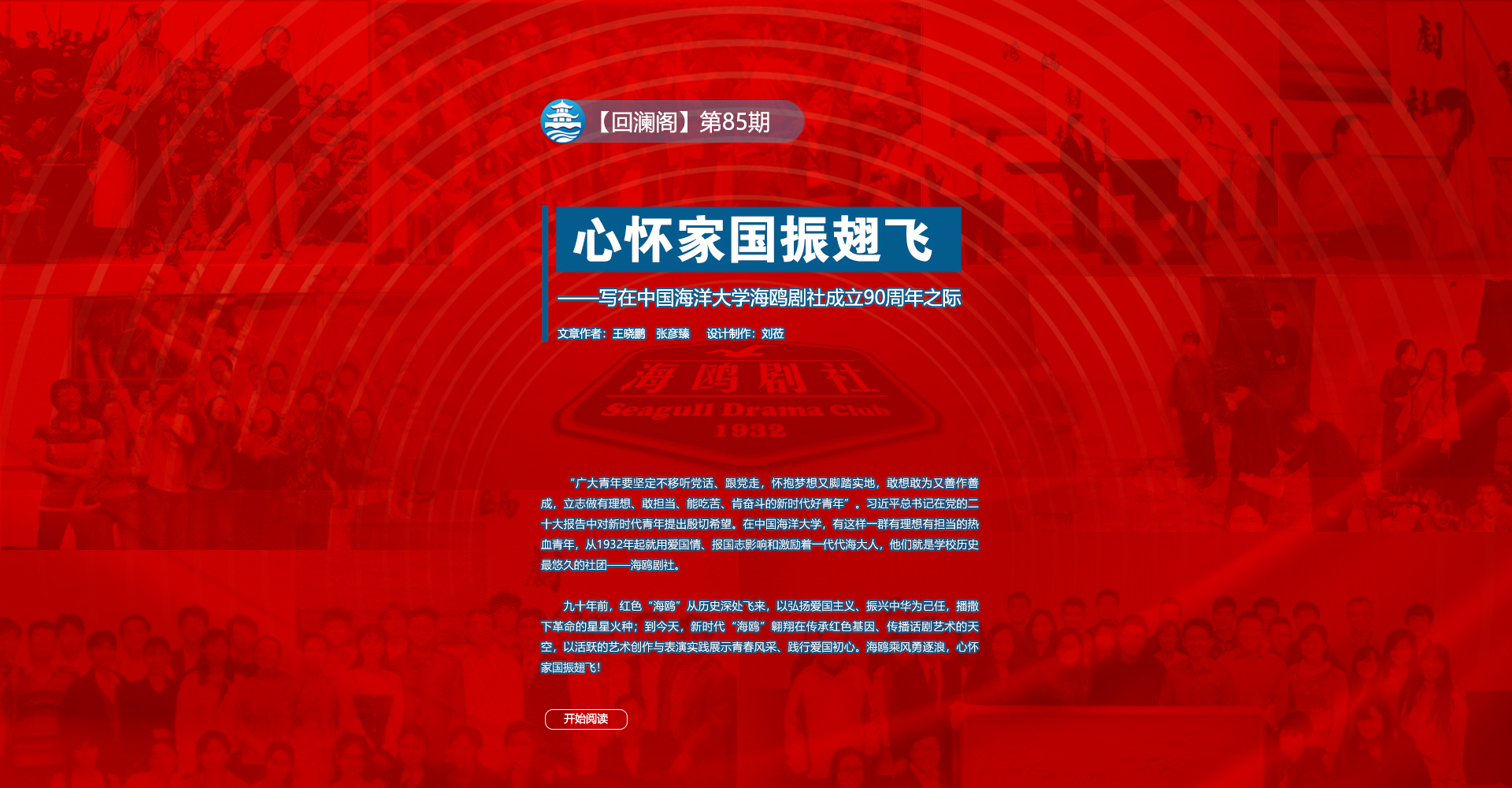【编者按】6月24日,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何沛东副教授在《光明日报》第14版“文史哲周刊•理论•史学”版发表题为《中国传统航海计程方法的演进》的理论文章。何沛东副教授梳理了主要以“月”“日”“潮”“更”“里”计程的中国传统航海计程方法体系及其演进历程,认为此方法体系不仅是千余年来中国航海技术持续发展进步的一个缩影,也充分展现了中国人在海洋探索中的非凡智慧和务实品格。全文如下:

随着人类航海活动范围的拓展,航程计算也成为必要的工作。在近现代船舶计程仪广泛应用之前,中国海域已经流传着一套主要以“日”“月”“潮”“更”“里”为单位的传统航海计程方法,为旧时中国航海活动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必要的技术保障。20世纪60年代,向达先生整理《两种海道针经》时提出“中国古代航海上计算里程的单位是更”的观点,之后学界对于“更”的讨论逐渐增多,期间也会提及以“日”“月”“里”等计程的史实(如朱鉴秋:《海上计程单位和深度单位》,《航海》1981年第1期;周志明:《中国古代“行船更数”考》,《古代文明》2009年第2期),近年来学界对于以“潮”计程的解析(何沛东:《试析中国古代的航海计程单位“潮”》,《自然科学史研究》2018年第4期;刘义杰:《“潮程”试析》,《国家航海》2021年第27辑),使中国传统航海计程方法体系及其发展进程得以完整地呈现出来。
文献关于先秦时期航海活动的记载过于简略,当时人们如何计程我们已无从得知。秦汉时期,计时单位“日”“月”开始被用于航海计程,如《汉书·地理志》详述了沿两广海岸西行经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洋的航路,“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六朝时期,法显“浮海东还”,舟师在南海迷失航路,“常行时正可五十日便到广州”,但经七十余日却仍不见岸(《佛国记》)。直到唐代,以“日”“月”计程依然是文献记载的主要航海计程方法,《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广州通海夷道”,除广州至屯门山的航程计算使用“里”以外,其余海上计程均用“日”“月”。但以“日”“月”计程存在一个不可忽视的缺陷,即由于其计量尺度过大而不能较好地适用于近岸短距航海,因此以“日”“月”计程的记载多为长距航海。
晚至宋代,在对潮汐知识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沿海民众发明了以“潮汐”计程之法。“潮”也成为一个航海计程单位,其本义是“以两地航道沿途潮汐相继发生的次数(或需要候潮的次数)表示航程的远近”,潮汐“自涨而落或自落而涨”为“一潮”。如淳熙《三山志》就明确指出“水路,视潮次停泊,犹驿铺也”,并以“一潮”“二潮”直至“十五潮”这样的潮汐累积数值来表示自迎仙港至莆门寨的航程,且在每一潮次之下均对船舶经行的海道、停泊位置等情况进行详细说明。宋代以后,虽然作为航海计程单位的“潮”在文献中出现了诸如“潮汐”“潮水”“汐水”等多种表现形式,但其基本用法却简化为“某地若干潮到某地”或“某地到某地若干潮”,如笨港“北至海丰港水程一潮”(康熙《诸罗县志》卷7《兵防志》)。当然,或是出于提高准确性和实用性的目的,“潮”也常同里数及风向、风力的相关描述联合使用,如“温州府至盘石,顺风半潮,约四十里”(《温处海防图略》卷2);络华山至壁下山、石衕山,“风水顺便,半潮可到,风水稍逆,便用一潮”(开庆《四明续志》卷5《烽燧》)。此外,以“潮”计程在具体表述方式上还会出现一些变体,但内涵并无不同,如《广东海防汇览》对于“海口往崖州水程”的记述,“潮一流至东水……一流至马袅”。由于我国沿海潮汐类型多为半日潮,一昼夜大概发生两次高潮两次低潮,且潮汐涨落历时基本相等,即大致将一昼夜的时间分为4等份,因此以“潮”计程所用的时间尺度较以“月”“日”计程更加精确,以“潮”计程也成为宋元时期我国东南沿海近海短距航行常用的计程方法。
到了明代,“更”已经被广泛运用于航海。“更”原本为夜间计时单位,一夜5更,在被用于航海计程时,正常情况下一昼夜为10更,一更约等于今2.4小时。对于航海活动中所用的“更”的性质,学界还存在争议,如为计程单位、为计时单位、为航速单位等。文献中常出现一日行船超过10更的记载,如“十一日并夜西南风,用子癸十二更”(《指南正法》),因而不能简单地将其理解为计时单位;受古代造船技术的限制及风向、风速、潮流等因素的影响,即使是同一船舶在不同时段航行于同一航线的速度也难以保持一致,文献中一更约合50里、60里甚至90里等的差异即是此种情况的显著体现,因此“更”为速度单位也不合理。旧时人们在船头向海中投入木片,人向船尾“疾行”(或“行”),若与木片同时到达船尾,则为“标准更”,曰“合更”或“上更”,此时一日方可约为10更,否则为过更或不及更,需要相应减少或增加航行“更”数才能到达指定的位置,上述一日行船超10更的记载即是因过更而“兼程”的结果。由于船舶航速难以准确测算出具体数值,而行驶时间则可以通过沙漏或“以焚香几枝”获知,因而舟师将船舶以“标准更”的航速在一更的时间内经行的航程通过一更的时间内涵表现出来,此时的“更”实则具备航速、航程和时间三重内涵。以“更”计程即是将“更”的时间内涵作为计程的基本尺度,依据船舶航行情况,适时调整行船“更”数,最终以“更”数的累积值表示航程远近,此即王在晋所谓的:“更者,每一昼夜分为十更,以焚香枝数为度,以木片投海中,人从船面行,验风迅缓,定更多寡,可知船至某山洋界。”(《海防纂要》卷2)当然,“更”的时间尺度进一步缩短,其在航海计程中也更具灵活性,既可用于短距航海,亦可以分段计程的方式用于长距航海,且不受海域范围的限制,在明清时期的航海活动中应用最广泛。
至此,一套以“月”“日”“潮”“更”为主要单位的传统航海计程方法体系初步形成,此套方法体系中存在着一条以时间因素为标准的操作路径,大致依据航行时间、航向和主要参照物来确定航线和位置,简易且实用。从传统航海计程单位的发展来看,月(一般为30日)、日、潮(约1/4日)、更(约1/10日)背后的时间尺度越发精确,可见中国古代航海计程技术的不断进步,也反映出日益发展的航海活动对于航海技术精确化需求的持续增长。
除此之外,旧时陆地计程单位“里”也常被用于航海计程。但当时的人们大多认为“汪洋所在,杳无山影,非同内洋有涯岸垵泊者比”(《广东海防汇览》卷38),远海航行“不可道里计”就成了共识。诸如“千余里至对马国……又渡一海,千余里至末卢国”(《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等的记载,具有明显的夸张或臆测成分,在航海实践中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一些文献在以“月”“日”“潮”“更”计程之后还会说明“里”数,但所载里数大多是一个约略的数值,此种记述方式可能仅仅是借用广为人知的“里”让人们对船舶行驶的“更”(“月”“日”“潮”)数有个大致的距离概念,如康熙《重修台湾府志》记载台湾府到澎湖“水程四更”后的注释就明显具有此种意味,曰:“水程无里铺,舟人只以更数定远近。一更,大约旱程五十里。”
“月”“日”“潮”“更”作为航海计程单位出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但在中国航海计程的发展历史中,并没有出现后者依次替代前者或先进替代落后的现象,它们与“里”常会同时出现在某一段航程的记述中。而舟师对于航海计程方法的选择和运用会考虑到不同航线、不同海域的具体情况。船舶在近岸海域航行和出入港口,容易受到潮汐涨落的影响,常用“潮”作为计程单位;而远海航行受潮汐涨落的影响较小,且航行时间一般较长,所以需要用到“日”“月”或“更”进行计程。如万历《温州府志》载“大陈山乘东北风一日可至邳山,……自大鹿半潮可至横坎二门”,大陈岛距离邳山岛较远且两者远离海岸,因而以“日”计程;而大鹿岛距横坎二门较近且靠近海岸,因而用“潮”计程。当然,古人认为“海不计里”的关键问题在于没有合适的岛礁等做参照,但在一些海岛、港湾分布较多且距离适当的近岸海域,以“里”计程也可以做到相对准确,如旧时沿庙岛群岛至朝鲜半岛的东北亚航线,分布着较多岛屿,岛屿与岛屿之间、岛屿与陆地之间的距离也相对较近,因而此条航路的航行活动多是以“里”计程,《新唐书·地理志》所载的“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即是如此,而从宁波横穿黄海到朝鲜半岛的航路因几乎无岛礁做参照则是以“日”计程为主。清人陈良弼甚至讲,“有垵可泊有程可考”的“垵边之船,亦询及更数”是“因愚以诱愚”的糊涂之举(《水师辑要》)。道光《厦门志》卷4附载的“台澎海道考”“南洋海道考”“北洋海道考”,就显示了不同航线所用计程方法的差异,厦门北到北关、南到南澳的短途近海航线,所经港湾、岛礁众多,计程主要使用“里”和“潮”;而厦门东到台澎、北到宁波、上海、天津的远程或外海航线,则主要是以“更”计程。
将航行时间用于计程并非中国古代所独有,古代波斯、阿拉伯、印度的航海者也发明了以“法尔萨赫(Farsakh)”“扎姆(Zam)”计程的方法(陈晓珊:《郑和下西洋前后中国航海指南的变迁》,《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第1期),分别代表1小时和3小时的航程,但它们仅是作为单独的航海计程单位出现。而中国传统的航海计程方法主要由多种表示不同时间尺度的计程单位组成,并辅以陆地计程单位“里”,已经形成一个较为成熟的技术体系,能够满足远海、近岸、远程、近程等各种航海活动的需求,不仅是千余年来中国航海技术持续发展进步的一个缩影,也充分展现了中国人在海洋探索活动中的非凡智慧和务实品格。
(作者:何沛东,系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旧方志海图的整理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编辑:左伟
责任编辑:李华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