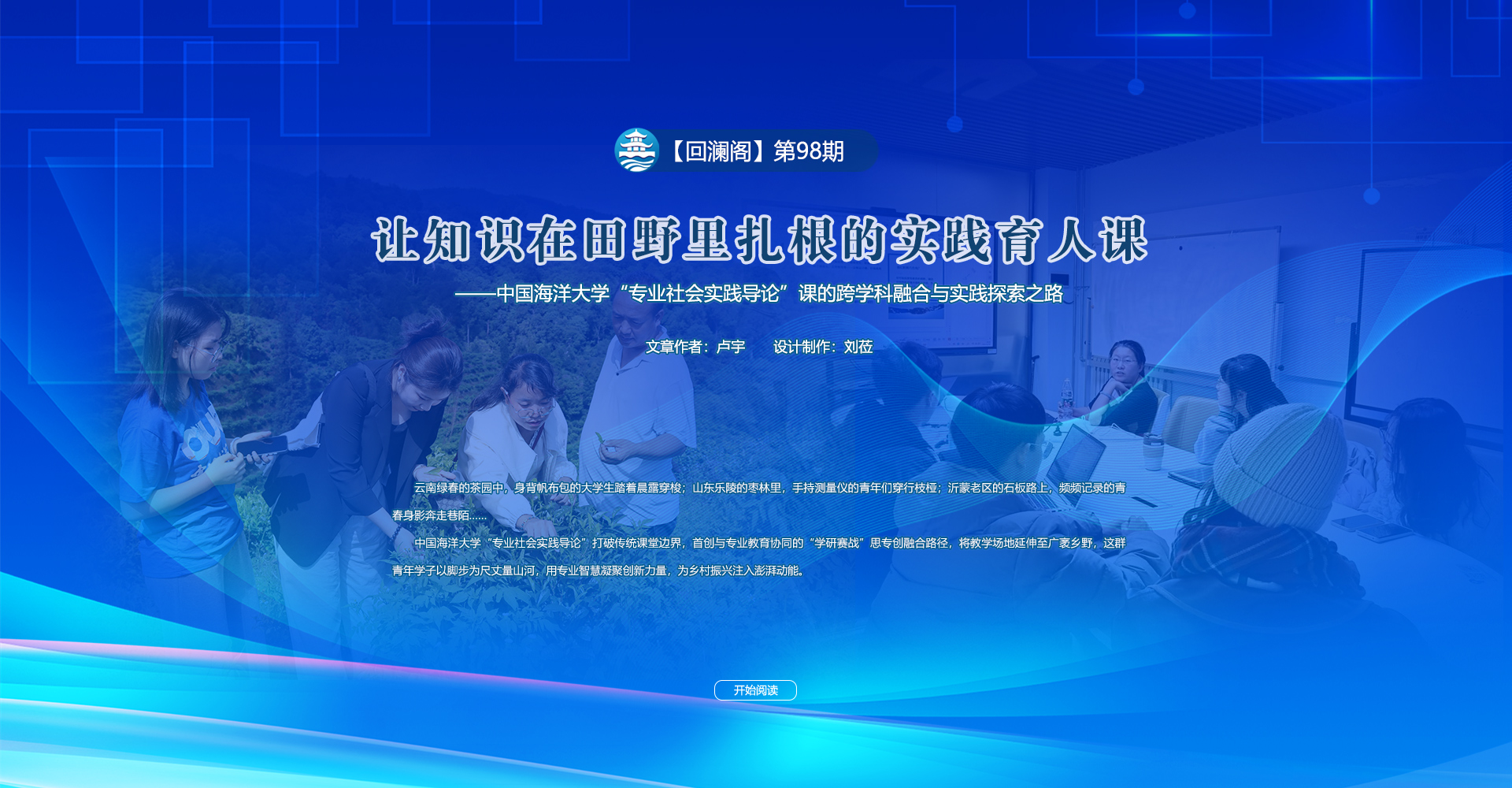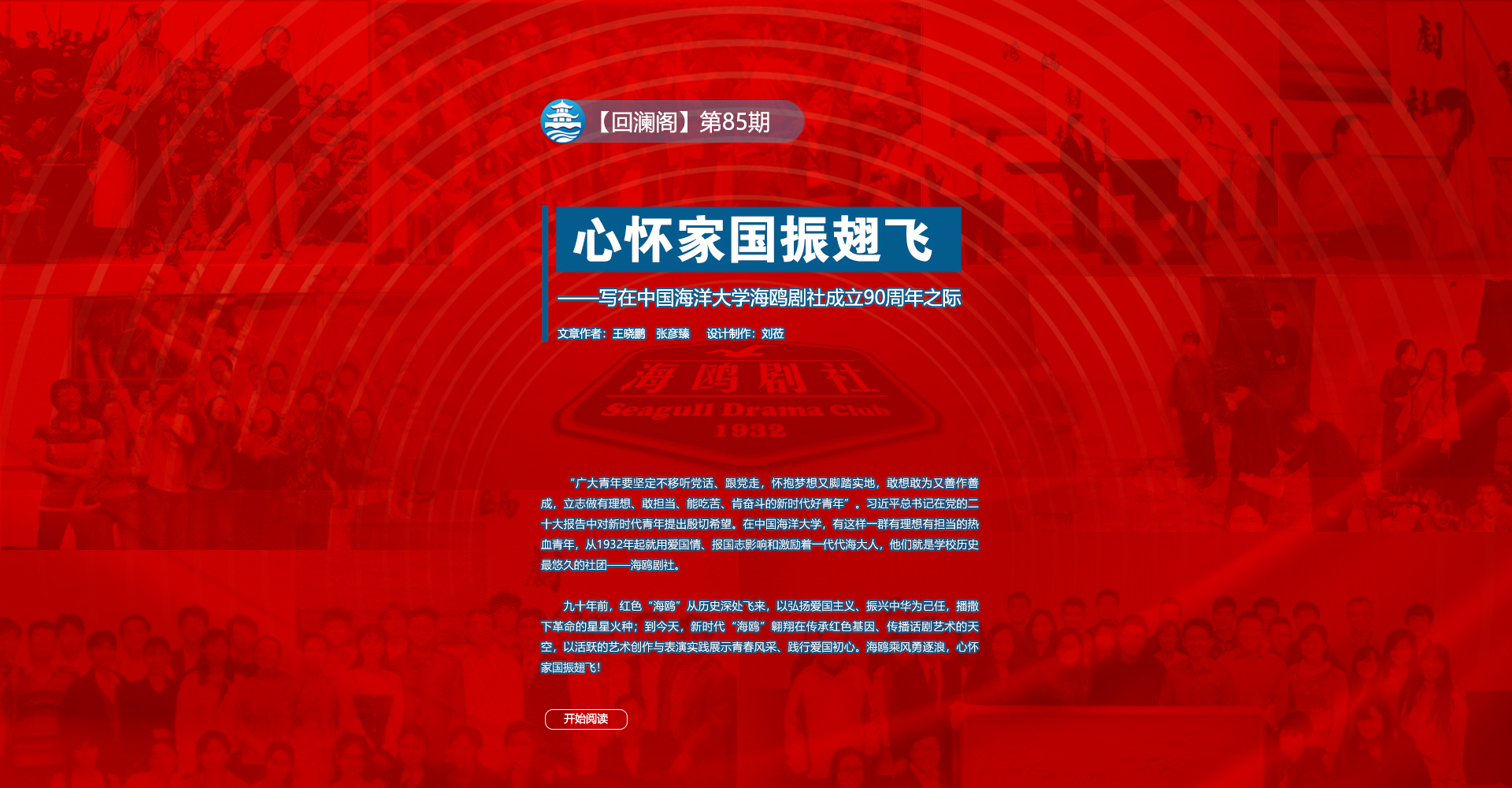本站讯 5月29日晚,由海鸥剧社主办、承办的话剧《红玫瑰与白玫瑰》在中国海洋大学大学生活动中心上演。该话剧改编自张爱玲的同名小说,讲述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从西洋留学归国的佟振保与老同学风情万种的太太王娇蕊擦出“欲望之火”。但当她将真心交付,他却因不想承担责任、落下坏名声,而转头同自己并不喜欢的循规蹈矩的孟烟鹂结为夫妇,并展开了一段痛苦的婚姻生活。
引子
“每个男人心里都至少有两个女人,一朵红玫瑰,一朵白玫瑰。”
大幕拉开,华灯骤亮。一方舞台,左右错落。两位女子身姿翩翩,分立两侧。
铁艺桌椅,一席青衫。白衣清冽,轻扯丝线,似有道不完的思绪。
皮质沙发,短衫洋装。红衣妩媚,小酒细酌,如丝媚眼勾贪念。
舞台中央几道白色拱门,划分了空间的界限也分隔开了两段不一样的人生。

红玫瑰——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泪水
“用鲜辣潮湿的绿色做旗袍,再露出粉红色的衬裙”。王娇蕊是一个风情万种,热烈奔放的南洋姑娘。她微微抬手,轻拢鬓边,扭动腰肢,缓缓坐在自己丈夫的腿上,微启丹唇,声音轻快又甜腻:“你不是说,你同学快来了吗?”
佟振保推开一扇虚掩着的门,也顺势撞进了娇蕊的心房。人人都称王娇蕊是一朵交际花,她外貌姣好,身姿动人,喜欢自由,不爱约束。她似红玫瑰一样,热情地开放,热烈地去爱。红色的玫瑰,姿态婀娜芳香弥散妖异魅惑,勾勒着男人隐秘的幻想。
舞台上蓝光亮起,音乐像小雨般错落,滴答作响,撩人心弦。
“我的心是一所公寓房子。”
“我只习惯住单幢的。”
“看你有本事拆了重盖。”
当初看似调情的一席话竟与未来事态的发展不谋而合。王娇蕊不顾忌自己的身份是佟振保朋友的妻子,她爱就爱上了,奋不顾身。她要放弃家庭,放弃现在安稳的生活。于王娇蕊而言,与佟振保在一起,甜蜜又刺激。
爱情来临时,女人的选择总是一往无前。
“我恋爱了,爱上了你的老同学,他是个有作为的人,是一等一的纺织工”。王娇蕊是一个天真的南洋姑娘。她认为她不顾一切爱佟振保,佟振保就会不顾一切爱她。她天真地以为隔在他们之间的只是一纸婚约而已,她没有注意到振保的迟疑,她没有想过他愿不愿意娶她。
选择爱情的她,什么也不顾了。
不惧世俗,勇敢追求。一朵热烈的玫瑰绝不会放弃盛开。遇到真爱时,娇蕊知道受伤是必然,但她依旧选择义无反顾。她拥有天真的头脑和成熟的身体。她可以做热烈美好的情妇,但绝不可能成为振保生命中贞洁的妻。
“她太沉了,我得把她扔了,啊,她压的我喘不过起来”。王娇蕊是一个傻乎乎地南洋姑娘。舞台灯光汇聚在佟振保周围,宛如世俗的目光赤裸裸地扎在他的身上。
迫于世俗的压力,面对佟振保的抛弃,她也想用眼泪当武器。她抱着佟振保的腰腿哀求。如同一个含冤的小孩,倾诉自己的不舍,梦魇呢喃一般的重复着“我改,我改”。
似火般的红玫瑰没有了,留下来的是一位平淡的女子。她安安稳稳地成家,因为孩子牙疼折腾许久,早起奔波。岁月的磨砺使得王娇蕊成熟端庄了许多亦苍老了许多,曾经原始而热烈的爱欲,如今已转化为平静而坦然的温情。
幸好最后她学会了爱。
昏暗的舞台灯光下,王娇蕊缓缓道来:“爱到底是好的,虽然吃了苦,以后还是要爱的,所以我不过是往前闯,碰到什么就是什么。是的,年纪轻,长得好看的时候,大约无论到社会上去做什么事,碰到的总是男人。可是到后来,除了男人之外总还有别的……总还有别的……”

白玫瑰——宛若明月光,可望不可即
“我是一个可爱的女人,白,稀薄,温热,像是冬天里,自己嘴里呵出来的一口气。”孟烟鹂是一个单薄细长,面容宽柔的传统女子。不同于王娇蕊的热烈,孟烟鹂宛如一抹皎白月光,总是安静地立在那里。时而局促地搅动手指,时而用一方手帕微微掩面轻笑。
她温顺内敛纯洁贞静,是佟振保名正言顺的妻。
“可我的丈夫振保看不出,他不要我,然后我就飘散了。”孟烟骊总是怯生生地站在丈夫的身后,因为她自卑,因为她总是笨。她是生活在框架里的姑娘,性格乖张,从无交际,不懂幽默。她爱佟振保,爱得理所应当,不为别的,就因为在许多人之中指定了这一个男人是她的。
可他们原本应该是一个亲密的结合体,却因为灵魂无法共鸣活的像两个陌生人。
白玫瑰是圣洁、美丽的。但是被俗化了之后也只是一粒粘在衣服上的白饭粒,让人提不起半点兴趣。和王娇蕊相比,孟烟鹂显得单薄而平庸,既缺风韵也乏朝气,不免使人倦怠乏味,成了让佟振保烦腻不已的累赘。时间使烟鹂变成了一朵没有悲伤和愤怒的白玫瑰。她承受着复杂和琐碎的压力,却换不来丈夫的正眼相看。
人一旦有了隔阂,就很难再亲近。
“还从来没人,说过我聪明呢。”孟烟鹂的改变只因裁缝无意间的一句话。全世界里只有佟振保的那股荒唐劲结束了。烟鹂的背叛或许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向来只会被否定的她第一次尝到赞美之词的甜蜜,于是她贪婪地放任自己深陷其中。
可是烟鹂始终是脆弱胆怯的烟鹂。她小心翼翼地和裁缝私会,但那暧昧的神色、游移的目光很好的说明一切。雪白的花瓣倾落而下,落在烟鹂的柔肩秀发之上。爆发式的争吵过后,孟烟鹂还是选择了克制,亲手扼杀了自己难得的热烈。
明月光,清淡幽远,可望而不可及。白饭粒,不觉珍贵,却不能缺少。

佟振保——红若成嗜 白渺如雾
佟振保总力图创造一个“对”的世界,“我叫佟振保。我从英国留学回来,在英国人办的一家鸿艺纺织公司做事。”“因为她是王士鸿的老婆。王士鸿是我的老同学老朋友。我佟振保是个做怀不乱的柳下惠。”“我想起我在爱丁堡读书的时候,家里怎样为我寄钱,母亲怎样为我寄包裹,现在正是报答的时候,我要一贯的向前向上。”而振保乙偏偏喜欢发泄,“调情呢,跟女孩子聊天你得聊点儿衣服啊香水儿啊还有胸啊……”“但你想占有一个女人身体的时候,你会对自己说,爱上的是她的灵魂。可是你别忘了,要想得到她的灵魂,就得先得到她的身体。”唯一相同的是他们都不是什么好人。佟振保和振保乙都贪恋着身体的重量,却把红玫瑰花变成灰褐色流线型的大屋,“像大得不可想象的花车,朝我轰轰然开过来。”却让白玫瑰花做了他们身下、屋檐下的奴隶,“人家生了孩子都变得丰满了,可是你还是那么瘦。”不过无论如何,白玫瑰怎么可能会像一朵红玫瑰呢?
烟鹂听了振保的话去学普通话,她三天两头就要换仆人,因为待在振保身边老挨骂,连仆人也容易看不起她。到了最后,那个小裁缝也被她阻在门外不让进了,因为她爱振保,也就不要人夸她聪明了。佟振保还有脸去找王士鸿打牌,并谈起了以前那朵红玫瑰。“士鸿老同学,你现在还带着娇蕊的照片吗?”“有啊,毕竟夫妻一场嘛,但听说她又结婚了,嫁给一个姓朱的。”
重逢在一趟公共汽车上。
此刻,舞台上苍白刺眼的灯光集聚在身着一黑一花衣裳的两位女子身上。王娇蕊朝佟振保勾了勾头,欠了欠身,他才认出面前这个妇人。毕竟她是大变样了,带着孩子们去看牙医,也老实爱一个丈夫。就像烟鹂,她的嘴变得很泼辣,碎碎念念再不是以前的样子了。
不知道为什么,佟振保在公共汽车的镜子里看见他的眼泪,滔滔地流下来,有一种奇异的命中注定的感觉。
既然要了理性,那便抛弃那热烈的欲望一头扎进寡淡温和的白水,这样的生活看起来无疑正确,但是明明一切都是自己选择的,却像是被更厉害的角色玩弄于股掌。佟振保、振保乙,他们总有不同的意见,他们让他不断摇摆,摇摆在两朵花中间。但他们并不会分裂,今夜,佟振保可以捂死振保乙,明天振保就可以改过自新变成一个好人了。他是真才实学的留洋人,是一个好丈夫,已经养了妻子九年还要继续养下去。是一个好儿子,侍奉母亲谁都不会有他那么周到。万一要是腻了的话,明夜让振保乙捂死佟振保好了。
只是无论如何,振保他不会再天真了。
灯光渐落,人物就此隐身在一片浓郁的黑色里。剧目在一片寂静中忽然结束,不久,等观众反应过来,台下爆发出了阵阵热烈掌声。
“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 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变化更迭的时代带来了些欲望,但还具备遗留下来的杀死欲望的能力,以至于男男女女都在这场荒诞中不甘却无奈地死去,不过不是全部地死去,能苟活的那个自己会留下来。人们歌颂的象征着中西交融新开放的爱情和一些其他什么都被捂死在红白花瓣落下的瞬间,它们变得遭人嫌弃,被从衣服上抠下来轻轻弹开。
张爱玲笔下的佟振保也始终走不出那个困境。他周旋于理智与情感,也站在理想与现实的节点,堕入无限上演、永无止境的痛苦。
而在这一场场自我与本我的激烈角逐面前,我们又该如何抉择?

图:陈博健 刘一韬 刘江民 文:杨岚 彭瑀珂
编辑:王彦博
责任编辑:赵奚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