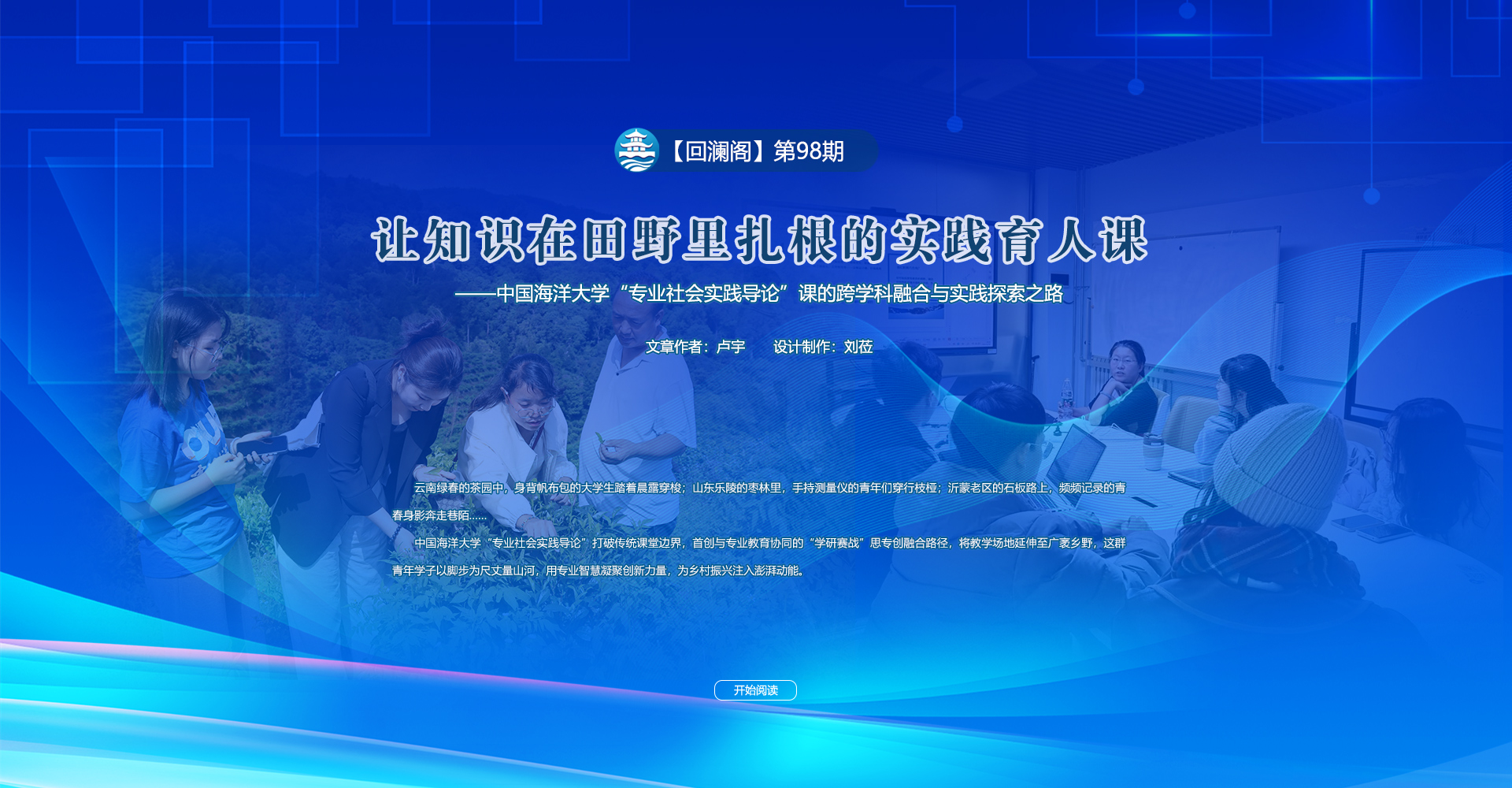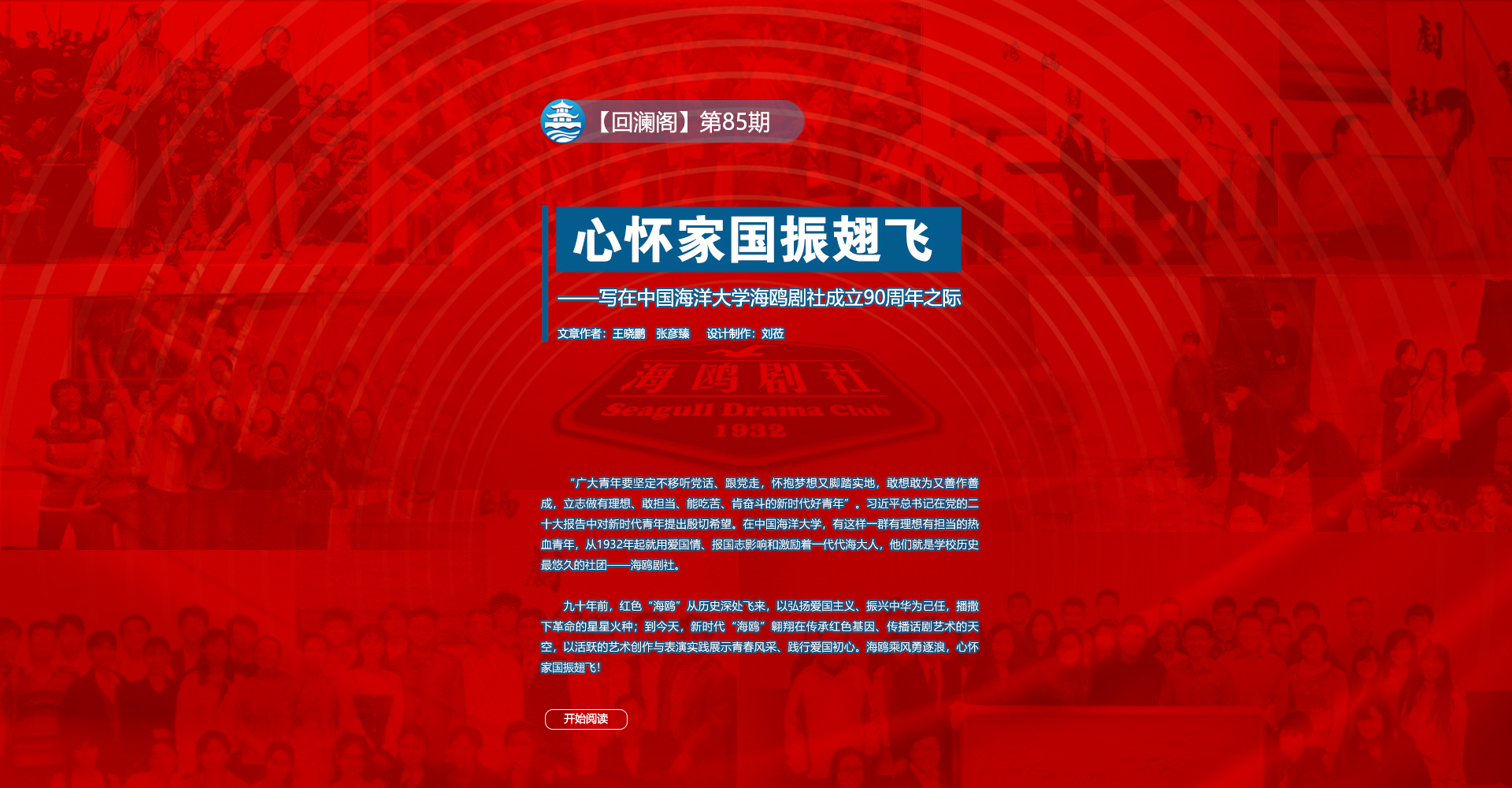父子争执
本站讯 5月26日晚,由海鸥剧社主办、承办的话剧《生死场》在大学生活动中心上演。该话剧改编自萧红女士创作的同名中篇小说,以村庄的各个家庭为“平台”,勾绘了东北农民贫苦无告的日常生活,描述了一些女人在男权世界里卑微而无助的生活与死亡,对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前后黑龙江农村乡民“生”与“死”的故事进行了演绎。话剧主要展示了封建文化熏染下乡民糊涂、芜杂的生活状态。
序章
雪花纷纷扬扬,风声隐隐呼啸,唢呐悲怆寒凉。火盆透出一丝并不温暖的红光,掩映着四个聚拢在旁取暖的农民装束的男人,他们姿势迥异,神情却一致地麻木。一人一句的抱怨表达着对严寒天气的不满:刀一般的风,水缸也冻裂了,雪把房子封死了,从他们的抱怨中生活的悲苦于舞台渐渐展现。
此时,一束灯光照亮了角落上跪卧的妇人,妇人即将临盆,她无助地望向火盆旁取暖的男人,男人将火盆搬到妇人面前,男人无视妇人痛苦的表情,只关注到她肚里的孩子。妇人渐渐没了力气,男人们将妇人推来搡去,把她扛起,妇人悲戚而又无力反抗,只能接受这种粗暴的助产方式,他们欢快地唱起了生老病死之歌。
“生老病死,没啥大不了的。生了就让他自个儿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就算了。”
“老了也没啥,眼花就甭看,耳聋就不听,牙掉了整吞,走不动瘫着。这有啥法儿?谁老谁活该!”
“病,人吃五谷烂杂,谁不生病呢?”
“死也不是啥事。爹死儿子哭,儿子死妈哭,哥哥死一家子哭,嫂子死娘家人哭。”
生老病死在他们口中变得日常而平凡、麻木而简单,每送走一个生命,第二天也会迎来一样的日子。在这群人眼中,活着就是为了吃饭穿衣,死了就是一句简单的“完了”。妇人再次沉默,灯光渐隐,一声婴儿的啼哭声响起,屏幕上“生死场”三个字在红黑掩映中格外醒目,生命的结束,生命的开始。
承诺提亲
(一)殇起
一阵呕吐声传来,灯光打在了金枝娇小的身躯上。金枝抹净嘴,抚摸着肚子,慌张踱步,满脸愁容。成业的声音传来,金枝想要回家,成业用手环住想要逃跑的金枝,承诺一定会去提亲。金枝害怕爹娘会不同意,低声哭泣,却忽又抱住成业。
“成业,好成业,娶了我吧。哥,你娶了我吧,啊,哥,娶了我吧。”
“这算啥?不就是有了,娶你就是生儿子的,生,给我生满满一院子。”
金枝想起了因生孩子死去的月英姐,可成业毫不在意,灯光渐隐,只留下高高挂起的南瓜灯昏黄的光亮,渐渐垂下。
一阵犬吠声打破了夜的寂静,躲在隐蔽处手握镰刀的赵三与溜进柴房的男子一阵激烈打斗。最终,男子被赵三割喉致死。场景渐明,四个男人和赵三的妻子王婆围拢过来。还没反应过来的赵三身体打颤,呆呆伫立,不敢相信自己已经将眼前的男子杀死。
“她爹!你高高的,高高的,她爹!”激动的王婆剧烈喘息着,拍打着仍没缓过神的赵三,和众人一同让他相信“二爷”已死。
赵三陷入回忆中,不讲清理的东家二爷要求加租,他苦苦哀求也无济于事,二爷反用放火烧掉柴房相威胁,发起狠的赵三扬言要整死二爷,却只得来二爷哭笑不得的嘲讽。
灯光暗了又明,王婆将嘴里的水喷向发愣的赵三,他的思绪回到现实中,也终于相信了“二爷”已死的事实。四个男人与赵三快活地商量着与大家共享二爷的财产,畅快地勾画美好的未来生活图景,大家纷纷表示愿意追随赵三。赵三引导大家为二爷磕头发葬,希望二爷理解他们生活的苦,生老病死歌在众人口中洪亮响起,南瓜灯在一旁亮起,绽出开心的笑容,好似希望冉冉升起,却又透露着一种不知名的嘲讽。
“生啊! 就是老天爷和好了面,一屉顶一屉, 发面馒头(就是)来到世上蒸一蒸啊。”
“老啊!死面的饼,老牛的筋,除了阎王爷,谁也嚼不动啊。”
“病啊!就是破身板儿,可别死心眼儿,扛不住就给人撂挑子卷铺盖卷儿啊。”
“死吧!就是你翻白了眼儿,蹬直了腿儿,到了阴间啥也别扯,整明白了?”
赵三讨饶
歌声结束,掌声起,二爷鼓着掌从角落走出。赵三慌乱检查死人,发现竟是位长衫男子,众人颤抖着匍匐跪地,软弱不似刚才那般。二爷威胁要以杀人之罪将赵三抓起,赵三气势渐弱,
“二爷!您是我的东家,我一个人儿的东家,您放高了手饶我这回,饶我这回。二爷!饶命。饶命,二爷!“
看着伏地求饶的赵三,王婆气愤不敢相信,她的手颤抖着指着赵三,晕了过去。灯光渐隐,唢呐声缓缓响起。
(二)痛深
一阵犬吠声想起,金枝、成业两个年轻人拉拽着慌忙行走。望见自家柴房着火的金枝想要回去,但被成业制止。成业的爹二里半一瘸一拐地追上,让成业放弃出走跟他回家。成业不同意,僵持之中跟二里半拉拽起来,并将他撞到。成业以二里半将亲事提黄作为解释,向他磕了头,拉着金枝跑远。
熟悉的羊叫声引得二里半讲出心里话,“‘多儿多女多冤家,无儿无女活菩萨’是这理儿吧?他说我把他的亲事提黄了,他咋就不说,他让他爹我丢了多大的人!”,同时,二里半也陷入了为成业提亲的回忆中。
他想起成业求他和麻婆去金枝家提亲,而二里半支支吾吾说了一堆夸赞赵三的话就是说不出提亲的事情。成业着急,自己冲出来提亲,金枝被吓坏了,跪下急促的喘着粗气,晕了过去,成业抱着金枝跑走。成业与金枝跑远,赵三气愤无处发泄,猛回头看向了二里半。
哀求提亲
“二里半,胆子大,胆子大呀,原来你才是那个胆子大的啊。”
回忆止,无处发泄的二里半只好又向羊抱怨,却发现羊不见了。这是麻婆跑来刚要讲什么事情,却因为发现丢了羊而哭喊起来,烦躁的二里半打断了她,问她之前喊他是要说什么事情。
“哦对,刚才啊,可了不得了,赵三,他让人逮走了!”
得知赵三杀人,二里半想是因为他去提亲,赵三才气急杀了人。二里半想跑,王婆想到儿子不想走,磨蹭半天。这时警所官员带着日军过来,向二里半讨吃食。二里半觉得警所官员能够保护自己和麻婆,欢喜将他们迎进了家门,请他们喝了粥。这边二里半正与警所官员闲聊,警所官员无聊打起了瞌睡,二里半却十分兴奋。
“你们来了,早来两天呀,啥事就全变了,早来两天儿,这胆子还不就真大了,还怕他赵三?来了,来了好哇,多住两天儿。(又寻思)可晚了,该早来两天儿,早来两天儿……”
这时,麻婆衣衫不整地跑了过来,尖叫声仿佛要刺穿观众的耳膜,她哀号着向二里半哭诉两个日军的恶行。麻婆突然冲向一个日军,猛打起他。二里半愣住的同时,其中一个日军已慌乱中将刺刀扎向麻婆,麻婆大睁着双眼转头看向二里半,倒头死去。警官极具讽刺性的向二里半鞠了一躬,喃喃说道:“谢谢你的粮食,你的婆子。他们还说,是……你婆子,招呼他们进去的。”
二里半所有的愤怒涨满心中,走向麻婆俯身看她。二里半愤怒着、愤怒着,愤怒得抬手打了自己这已死的婆娘一个响亮的耳光。羞耻感使麻婆在凄冷中走向了死亡,二里半的懦弱和“面子观”一样断送了麻婆最后的希望。灯光渐隐,唢呐声声悲怆,生命的死亡似乎也是这样的简单、平凡。
(三)寂冷
警所一片漆黑冷寂,灯光照亮被关押的赵三,他卧地坐着,神情颓废而目光怨怒,口中咒骂杀人前的聚会——每个人都信誓旦旦要追随他,为他看好柴房,赞赏他的胆子大;而今只留他一人孤独地消受牢狱之苦。
二爷赎赵三
一阵敲击洋钱的响动声引出了二爷,他用五块大洋将赵三赎了出来。二爷进牢里看望赵三,赵三跪在地上仰望二爷,听到能回家的消息,眼中顿时燃起希望,对着二爷磕头道歉。二爷再提及加地租的事情,赵三不再反抗,反之磕头感恩戴德。灯渐隐,欢快的唢呐铜锣声响起,南瓜灯在地上亮着昏黄的光。
灯光再度亮起,舞台一边是出狱的赵三,另一边是望着油灯发呆的王婆
“王婆子,她娘!二爷拿了钱,二爷拿了钱哪!赎了,赎了咱出来。二爷是咱的恩人!大恩人!”
“我就没见过这样的男人,起初是块铁,后来咋是堆泥了呢?”
一人一段独白,婆子绝望而悲哀,赵三开心;赵三和王婆对金枝不同的态度,体现了男权社会中女性备受妇德压榨的悲惨境况,从此时起,王婆也已经对这个家和未来失去了信心,而此时不知情的赵三还哼着小曲,沉醉在重见天日的欢欣和回去让别人服软的快感中。对比如此强烈而讽刺。赵三哼着歌渐渐走远,寒风呼啸,王婆服了毒,大声的喘息着,瞪大了双眼。南瓜灯映衬,赵三的歌声还在继续。
金枝梦见了哭泣的王婆,她想回去,可成业不许,他觉得会丢人。
“回去丢人哪!你肚子里有了东西,远近地邻都清楚,那些婆子嘴里能有好?咕叨长、咕叨短的能闲着?我从小就被人戳点,不想再听见了!”
金枝想起从前几个婆子的议论及母亲对她的态度,颤抖着哭了起来。成业看着哭泣的金枝逐渐烦躁。与金枝又争吵起来。金枝望着眼前不断埋怨她的男子,绝望的向外走去。
“金枝,我不好,我嘴欠!你别走,金枝!”
两人的争执引来了宪兵,两兵将成业绑起来,拿出兵契,掰着成业的手按了手印。
“我们是自发军,请你加军,管吃喝、管粮饷。”
“老总,这是我媳妇。她肚里怀了我的种,我加军,她可咋活?老总!”
可宪兵并不听他的解释,以触犯军法会给他治罪相要挟,而心如死灰的金枝不愿理睬,只是木讷地转过身去。
“金枝,你见死不救!你咋不吱声?你等着,等我回来弄死你!弄死你…… ”
悲怆的曲子响彻舞台,悲剧仿佛还在继续,无数生命依旧在静默中走远。
众人戳点金枝
(四)哀绝
送葬的乐曲回响着,菱芝嫂与五姑姑升起一盏南瓜灯,一个男人铺放草席,其余几个架着死去的王婆,并将她放在草席上,众人喃喃咒骂着二里半和他“不清白”的婆子。舞台两边分立赵三和众人,赵三执手拿着二爷赠的酒,众人则围着王婆为其发葬。
“二爷,牛、皮袄也还不了您的情。我这辈子就怕欠情!欠了情就不安生了。您赎我拿了多少钱呢?老多了!我可咋还?”
“没法儿活,也活不好,二里半家他成业还敢私姘金枝,有钱可以,没钱也敢姘?没见过这样的人。”
赵三沉浸在对二爷的无限愧疚与感激之中,众人沉浸在熬不出的苦日子中,将二里半当做撒气桶,众人上前对他踢踢打打,二里半倒在地上不吱声,他的心里一样埋藏着对社会人情的悔恨:“晦气,晦气啊!三哥,你婆子死的烈性,我婆子死的臊性。我里外里不如你啊!我不清白,成业不清白,就连婆子死也不清白。造啥孽了?三哥,你在大狱里好吗?你清白,到死都清白。胆子大,到死都胆子大啊。”众生仿佛皆糊涂,不知为何起怨,亦不知为何泄气于人,不知为何而苦苦求生,也不知这摆在眼前的死亡到底是解脱还是遗憾。
这时赵三抱着酒坛子缓缓靠近,众人惊讶地确认是二爷将赵三赎出之后,将王婆服毒而死的事实告知了赵三,看着王婆的尸体,赵三顿时愣住了,仿佛不认识眼前的各种人和事,他迷惑于王婆因何而服毒。欢快的民乐响起,赵三回忆起杀二爷前夕。
王婆送他一支老洋炮枪,王婆佩服有勇气杀二爷的丈夫。赵三与王婆想着杀死二爷,两人开心的打闹着,放声大笑。
“咱不能让他加租。”
“不让他加租。”
“不能加!”
“不能加!”
“我不是孬种!”
“不是,她爹。”
他拒绝承认自己讨饶,他认识到了王婆死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软弱,他抱头痛苦,转而不愿承认。他宁愿他婆子是因为他杀错了人没了依靠,宁愿相信是因为金枝的离家出走。金枝回来,婆子突然瞪大双眼,一口黑血吐出,仿佛突出了她积埋已久的怨气。王婆醒来金枝与婆子相拥而泣。赵三嫌女儿成了泥,王婆安慰金枝,金枝疯狂对乡亲们磕头,卑微乞求求乡亲别戳点她。
“村儿里的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我金枝和成业相好,我肚里怀了成业的东西,可我想娘就回来了。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您几位放高手别戳点我,别戳点我肚里的东西!我给大家磕头了!”
而此时赵三只觉丢脸。灯光渐收,音乐渐停,故事好像进入了暂时的平静,却不知是暴风雨前夕那可拍的平静。
王婆苏醒
(五)惶落
蟋蟀声响起,灯光打在摇扇的二爷身上,二爷悠闲地跷着腿,为二里半读成业寄来的信。二里半蹲在一旁,侧耳听着,从信中知道了儿子去了自发军,最近在打鬼子;成业也交代请金枝别记恨他,也希望村里人别戳点她。二里半向二爷道谢后,却在一阵骚乱声后被二爷撵了出去。二爷拒绝收留日军在此处休息,最终被警员一枪打死。听到枪声的二里半不明真相,只埋怨自己不识抬举、不懂夸赞二爷。
“天暖了,全村都忙着生。生吧,都生孽瘴!小孽瘴变成大孽瘴,大孽瘴变成老孽瘴,生吧,生得全村儿人都不识抬举,都跟我一样的不识抬举。生,生吧,不识抬举,都生不识抬举的孽障哟…… ”
繁衍、生养以及生活,在二里半和赵三的眼中就是这样肤浅的定义,无关价值与意义,只在于攀附和面子,糊糊涂涂生,亦糊糊涂涂走到生命尽头。
刺眼的灯光打在金枝和王婆身上,金枝平躺着、双腿岔开准备生产,却迟迟不见孩子顺利产出。金枝痛苦的生产过程仿佛是受着刑法的“扭曲的艺术”,压抑的气氛充斥着全场,舞台上的生命脆弱得好像要走到尽头。二里半和赵三也憋闷地从两边走上前,纷纷埋怨孩子们做的事令他们觉得丢脸,让他们余生备受众人戳点,难以立足。
王婆燃亮一根火柴,火又熄灭,金枝的希望也仿佛随之熄灭了,她倍觉痛苦。二里半告知金枝成业捎信来说他加了军,挣了钱就回来娶她,却被赵三一顿数落。王婆为了让女儿顺利生产并活下来,手握镰刀恐吓女儿,怒目圆睁,随着乐声响起,金枝在挣扎中终于产下一女。赵三抱过婴儿,在一阵郁闷之后猛将婴儿掷出,婴儿啼了两啼,没了声响。
只听见二里半乐呵呵地大喊一声:“赵三,这下我不欠你了,咱俩两清了!”
舞台上的一切活动与声音都静止了,“生老病死”的歌再度响起。 金枝好像一具木偶,游魂一样转了转,费力爬向已无啼哭声的婴儿旁,抱起婴儿,一同死去。王婆在地上捧起不存在的黄土想把她们埋起来,已然疯癫的模样。悲怆的音乐冲击着观众的肺腑,让人的胸腔好似要炸裂般。
金枝痛苦生产
此时,远方打仗的成业,还不知道悲剧的发生,写信询问金枝近况,请求二里半不要怪金枝。
“爹,金枝该生了吧,就快了,打完这仗我就回去。可是这啥时候是个头?日本人咋就打起来没完,这信我就一直揣兜里,和大伙一样,想着最好别寄出去,真寄出去就真没盼头儿了。儿子不孝,没让你们享过福,临了了还让你们被戳点。不过您也别戳点金枝,她还要替我孝敬您呢。爹,你别一直喊老瞌陪你,多说说话,啊。儿先走了,也不知道还能不能从死人堆里再爬出来,等有机会再孝敬您。”
黑幕,一声枪响,成业身死,这是战争的残酷。大屏幕“生死场”三字亮起,红色的“死”字尤其亮眼。所有的有关生的希望犹如枯木凋零,所有关于美好生活的期待犹如灯油已尽的灯盏。生活还在继续,有的人虽然活着但他已经死了,糊糊涂涂不知为何生、为何死。这样的一生,在封建文化的熏染中,被深深地限制在一个“场”中,任何活着的生命都会窒息。
文:秦陈梦蕾 相振丽 图:李鑫淼 黄春闫喆
王婆失望服毒
编辑:系统管理员
责任编辑:系统管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