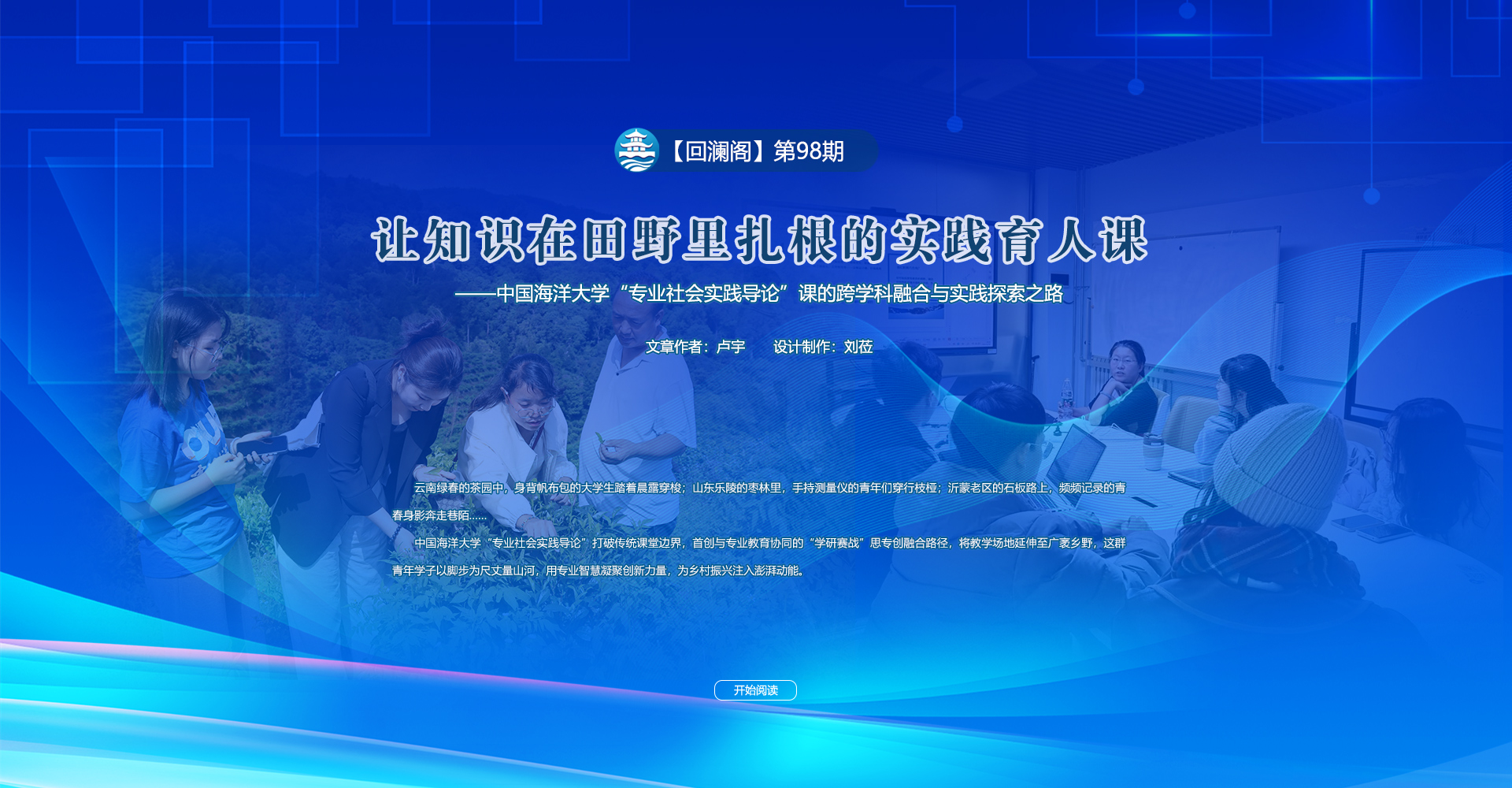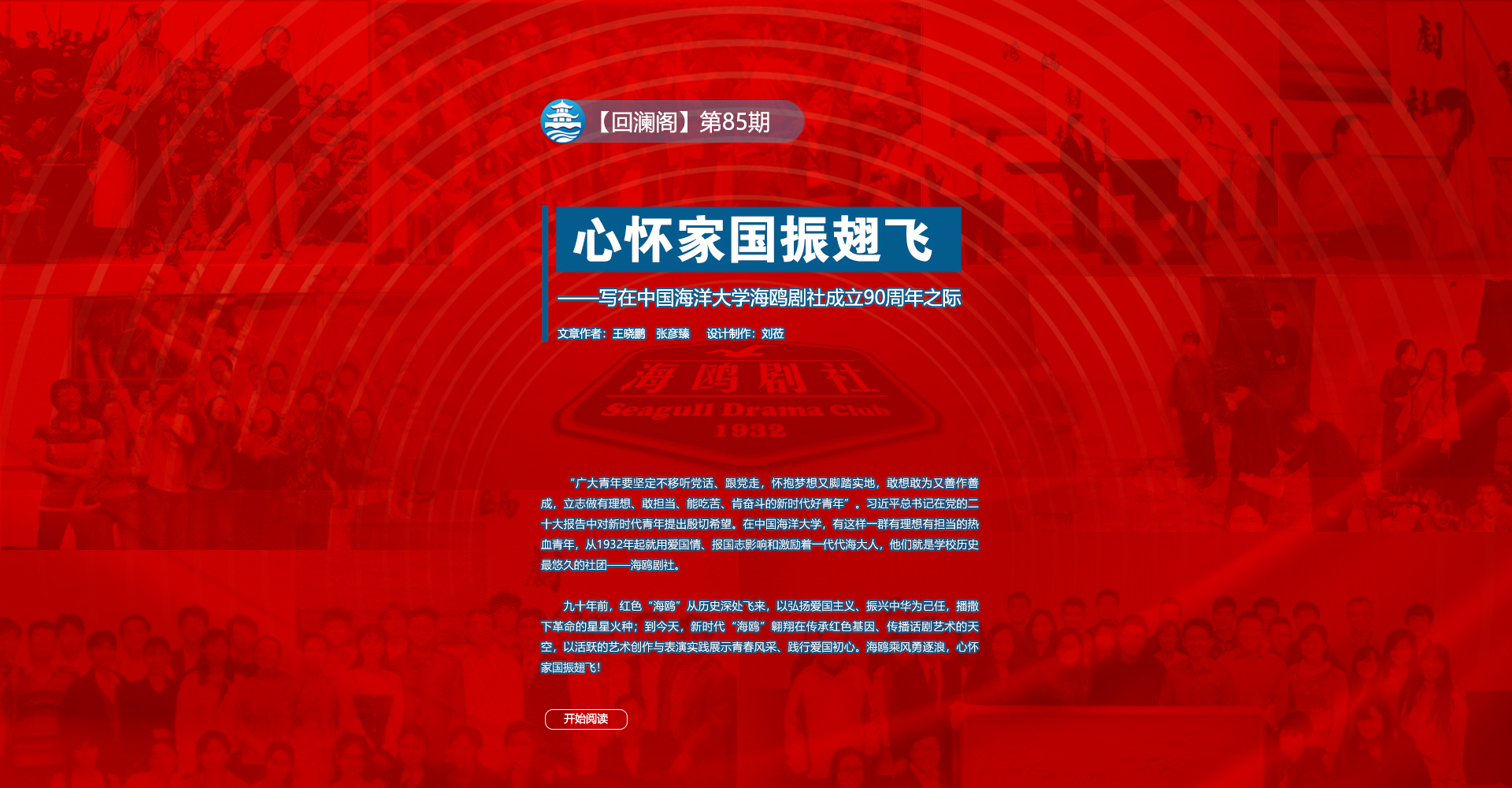日前,王蒙先生来海大参加了“王蒙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筹备会议。期间,文学院师生与王蒙先生就文学创作、人生哲学和道德修养等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5月19日(1348期)本版曾发表了座谈会的上半部分,本期再次推出下半部分——
王蒙谈人生哲学和道德修养
我的定位和哲学
问:《论语》开头讲“学而时习之”,你的《我的人生哲学》一开始也定位于学习,定位于自己永远做学生,沈善增送给你诗“天机参悟好心情,肆笑漠风作凤鸣。万水千山无厌足,只因定位是学生。”这与《论语》有联系吗?你为什么定位于学生?
答:我说“我是学生”,是因为给自己安上其它的称呼都不合适。如果我说我是作家,有好多年我并没有写作,前二十年没有写作,后二十年也没有写作,所以不能定“作家”。定“农民”,贾平凹已经抢先定了,定“工人”我也不像。只有定“学生”符合我的特点。虽然我已经快七十岁了,今天学了的东西,明天可能就会忘,但直到现在我也没有丧失学习的兴趣。我在德国的时候曾经学过六个星期的德语,虽然把德语完全学会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我至少可以用德语数到十。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德语单词反复地背到最后还是忘了,但是我对语言有兴趣,当一种语言我半懂不懂的时候,我会当音乐来欣赏,比方说英语,有美式发音,有英式发音,有印度式发音,还有黑人式发音,很有趣。
问:孔子把人的一生分六个阶段,王先生,你的一生你分为几个阶段?明年就是你的七十大寿了,你是否已到达“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阶段?
答:这是孔子就人生的大致情况讲的,至于我个人的情况,五十时离“耳顺”还远。六十也远远没有“知天命”也知不了。现在人的寿命延长了,所以人的青年时代相对往后推了,所以“知天命”和“耳顺”之年都会相对晚一点,至于“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更难做到了。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变化非常快,会不断发生一些问题,比方说“非典”这样的问题就很难避免,不能随心所欲。孔子的那种说法实际上适用于农业社会。农业社会相对简单,而现在应该更强调“活到老,学到老”,一天不死,就要迎接挑战,从必然的王国走向自由的王国。就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孔子提的那个标准我做不到。
问:人都希望能早一点大彻大悟,我觉得你已经做到。年轻时(比如30岁左右)能做到吗?没经过苦难的人能做到吗?有无办法让人较早的大彻大悟?
答:没有,我并没有达到大彻大悟,还远着呢。我说的当学生的意思,不仅仅指苦学读书、学外语,还特别包括对于各种实际经历的分析,尤其是反省。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做的成功的时候,都有做的不完全成功的时候,也有做的彻底失败的时候。在遇到具体事情的时候,是容易反省的。比如球赛,赢了也得总结,输了更需要总结。培养一种分析反省的习惯,在有些时候比读书还重要,这就是所谓“学习”。
问:你在书中说人生哲学是“天机、绝密”,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说出来就像下了地狱?
答: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一个人往往口头说的和做的不一致。“五四”的时候,对于封建文化,鲁迅说过“字里行间写的都是‘吃人’”。还有一个比较普通的说法就是“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的男盗女娼”。可是要谈到人生哲学,只讲口头上大家都知道的话,没有人愿意听。有些话天天都能说,但是如果要说出真实的内心体会来,又是非常难的。这种真实的体会,不是一种破坏性的,不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一类东西。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有某些自己不愿意说出来的经历。人不可能把自己的经历全盘托出,有不愿意别人知道的隐私部分,有非理想的权宜处理,这大致是正常的。人一生中肯定有自己也会为之汗颜的经验,除非那些无可救药的自大狂,自恋狂。讲述这些东西是痛苦的,但是当讲到对人生的各种看法时,都要尽可能讲得坦率,因为没有人愿意听非真实的道德训诫。
关于善恶等等的问题
问:关于“善”与“恶”的问题,想听王先生说说对问题的看法。善与恶是人人身上都有的吗?二者的本质区别是什么?二者可以相互转化吗?两个人、两个民族、两个国家有了矛盾,为什么常常是都只说对方很坏而不指责自己?
答:我认为人的本性谈不上“善”和“恶”,“善”和“恶”实际上是一种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和社会、文化都是分不开的,而且对于“善”和“恶”的理解也有明显的分歧。某个国家、某种社会、某个民族不能容忍的东西在另一个国家、社会则可能认为没有什么。比如中国封建社会认为寡妇再嫁是“恶”,现在我们则认为不让寡妇再嫁才是“恶”,这就说明对于“恶”的认识会有变化。但又有些最基本的东西不会变。一般社会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极度损害别人,甚至于损害别人的生命,恐怕认为这是“善”的就比较少了;随便杀人,强暴别人,在一般情况下,就不能说是“善”。而且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变成一个价值相对主义者,如果人人都认为自己是“善”,别人是“恶”,那就不行了。总归应有一个对整个社会的大多数人不起损害作用、破坏作用的标准。像“9·11”这样的恐怖事件,虽然恐怖分子也有他们自己的理由,但是我们对于那种大规模伤害平民的行为不能称之为“善”。尽管恐怖行为本身也很壮烈,他们开着飞机能那么平静地、准确地、科学地去撞大楼,这个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在目前的认识水平上,我们只能用粗线条勾勒出一个大致的标准。我觉得用一种最简约化的分析,就是起码不能无缘无故地去伤害别人,破坏别人。如果本性中总是有一种想损害、破坏、伤害别人的冲动的话,如果总是有一种敌视旁人的惯性,那么这就是一种“恶”的冲动。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嫉妒或是抢掠,都是应当摒弃的。
问:你在《我的人生哲学》中讲到“恶人者人恒恶之”,人为什么总是要以牙还牙而不愿相互宽容一些呢?
答:“恶人者人恒恶之”,也就是说你对别人不好,别人就对你不好。人世间很多事情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对别人抱有一种善意,就容易收获到善意;对别人抱有一种恶意,就会收获到许多恶意。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到处说别人坏话,别人一定也说你的坏话;关怀别人,从别人那里也能得到一种温暖——不仅是被关怀的人感到温暖,而且关怀别人的人也会有一种温暖的感觉。相反,对别人漠不关心,那么自己的生活也会非常低温、孤单。
问:有人说小孩从小为自己争东西,人天生自私,美国有人写过一本书,讲到有自私的基因,你怎么看待这类问题?
答:我认为这种提法用词欠妥当。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有保护自己的本能,要维持生存,必须保护自己。比如植物,这儿一棵树,旁边几棵草,也要争夺养料、水分和阳光。自我保护,维持生存,这本身不会注定成为“恶”,这是合理的。但是,用不正当的手段求得自己的生存,这是我们所不赞成的。所以,很多时候没有必要扣上“自私”的帽子。比如一个小孩子饿了,一定是自己先去吃东西,而不会先想到让别人去吃,这是一种求生存的本能——个体总是要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问:人有护短的本能,再加到处都宣传应学会包装自己,连学术批评都不说缺点,说到一点缺点也都说是“美中不足”,这样只讲优点,不讲缺点,人怎么样进步?你对此有何评说?
答:这是一种风气的变化。据我所知,目前幼儿园、小学里面做鉴定,互相都不提缺点,就是所说的“赏识教育”。这与我文章中的意思并不冲突。任何事物包括“赏识教育”在内都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比如作为质检人员,他们关注的一定是如何查处假冒伪劣产品;作为公安人员来说,他们必须以破案、治安为要务。而作为教育,特别是对幼儿和青少年的教育,多采取正面鼓励的方式,这还是可以理解的。至于文学批评,包括对于“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也应该是一种理想状态。我文章的意思是自己应当敢于暴露自己的缺点,他人的缺点只有他人自己暴露,别人没办法。当然也可能避免不了这样的情况,提倡暴露自己的缺点,反而有些人防得更严了。
问:我们都知道,不吃苦,不受挫折,人是难成才的。可现在的中小学教育在大力提倡“赏识教育”,这样能把孩子培养好吗?
答:不批评缺点,不等于将来不吃苦,不碰钉子,越娇惯,碰钉子的机会就越多。事实上,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还是需要吃苦的。因为整个社会没有义务捧着你、哄着你。人有时候会受到冷淡,有时候会受到冤枉,甚至有时候会受到侮辱,可能有的时候还会有突发事件——这些都是对人的考验。人的一生会遇到很多突发事件和被动局面,谁都不敢说自己一辈子总是占据主动地位,关键是碰到被动情况的时候能不能挺得住,能不能经过努力化被动为主动。
问:你是否注意到现实生活中有一类人,有了成绩都是他的,出了问题全是别人的,总说别人对不起他,对他评价不够高。这类人的思维方式怎么形成的?是天生的吗?
答:你说的这些人缺乏最起码的精神:反省精神。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反省精神,这是非常可怕的,这个人会变成一个非常可怕的人。因为任何一个人做任何事情都有做得好的时候,也都有做得不太好的时候,有主动的时候也有被动的时候。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体育竞技场上,对抗性强的项目中,肯定有赢的时候也有输的时候。人总有某些事情做得不太恰当的时候,认为事事都做得很好,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犯了错误以后,不愿承认错误,是要吃苦头的。即使是感情相当好的夫妻俩,没有一点互谅、互让的精神,在一起相处一个小时都是困难的。所以说没有一点反省的精神,没有一点互谅互让的精神,没有一点妥协的精神,最后的命运是非常悲惨的——或者是发疯,或者是进监狱,总之是要吃大苦头的。
问:有个哲学家说过人类头上有“三把刀”,不少人被三把刀杀了,这三把刀就是权、钱、色。还说权力对人的腐蚀是绝对的,大权力大腐蚀,小权力小腐蚀,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蚀。你如何看待这三把刀?
答:我认为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实际上“权”也和其他东西一样,既可以办坏事,也可以办好事。应当警惕权力对人的腐蚀,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反过来说,一个社会能不能没有权力的存在呢?当然不行,那就等于要求一个无政府的社会,一个无政府的社会更可怕。有一个符合理性的权力的存在,对于整个社会可以起到一个调解、维护的作用。就拿“非典”来说,接触过非典病人的人要被隔离,没有一点权力甚至强迫,是不可能办到的。没有人愿意被隔离,没有人愿意自己得病,但自己得了病又都不愿意被隔离。人具有这点自私,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了更多人的生命健康,这部分人就必须被强制隔离。
问:人从单纯走向成熟是规律,可有不少人到老也不成熟,比如有的人喜欢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喜欢背后添油加醋地议论别人。这类人为什么不能走向成熟呢?
答:人成不成熟不完全取决于年龄,像我们前面说过的那一种绝不反省的人,就永远成熟不了。人要成熟,反省是一个很重要的手段,还要靠学习。一个拒绝学习的人,一个绝不反省的人,一个永远和别人格格不入的人,就不会变得成熟。
问:在商界和官场上,有些人表现得似乎很成熟,可又像很圆滑,二者怎么区别?
答:有很多概念意思很接近,比如“单纯”和“幼稚”,“单纯”是好词,“幼稚”就不是好词。至于“成熟”和“圆滑”,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区分的尺度:一个人如果他保护自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他损害别人,就不应该原谅了。像《鹿鼎记》中韦小宝那样的市井地赖,做人也有自己的底线,那就是不出卖朋友。像这样的人也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问:有人说现在的社会是老实人吃亏的社会,许多家长教育孩子不能吃亏,有好事要争,不能让。所以现在公共汽车上给老人让座的极少。你认为老实人真的吃亏吗?
答: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但却是事实:就是对于“恶”的认识程度。一个人如果只知道世界是善良的,不知道“恶”的一面,那么他就显得幼稚了。如果一个人知道了“恶”,陷入了“恶”,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也很难说是理想。一个人了解“恶”的目的应当是为了超越“恶”,或者说克服“恶”,转化“恶”。了解“恶”不是为了自己也变得同样“恶”,或者更“恶”,这是有区别的。如果所说的“老实人”,指的是敢于把自己的真相告诉别人,暴露弱点,那么,从长远来看,我相信一个相对坦荡的人是不会吃大亏的,相反更多的人会理解他,同情他,甚至赞成他。但如果了解了许多的“恶”,而变得更“恶”了,那就是在“恶”的混战中当了牺牲品。
问:有人说人一生最难保持的是童心,因为童心纯正无邪,因为人成长的过程是被污染的过程,你对这个问题有何评论?
答:对于童心我的理解是这样:从审美的角度来说,童心是值得褒扬的。比如一个小孩子,他描述美好的亲情,说看到花开了,树叶绿了,他觉得很好。所谓“童心说”,是从审美角度来讲的。但是从其他角度来讲,是没有用的。比如医生,面对“非典”病人的时候,他需要的是医术,而不是童心。作为教授,首要任务就是教好书,当然在课余时间,如果具有童心的话,和学生们一块打打球,玩一玩,乐一乐,那就更好了。我们需要的“童心”不是一种“废品”,而是要以能够完成自己的使命为基础的。
问:在现实社会中下级对上级总喜欢报喜不报忧,大家都知道这是很不好的风气,但为什么这么难改变呢?
答:您说的这种情况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责任和监督的问题。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下级负责必然产生这些问题。领导来了就先把领导哄好了,领导爱听成绩爱听好话,领导一来就汇报成绩让领导听了高兴,对汇报的人来说也受到很大鼓舞。相反的,领导一来就汇报难办的事,领导皱着眉头,挺憋气的走了,汇报的人准没戏。还有就是监督的问题,不报实际的情况,还可以通过其他各种渠道——报刊、电视等媒体,还有信访等方式,使问题传上来。当然也有其他原因,与奖励机制也有关系,如果总是奖励说大话的人,而不惩罚虚报成绩的人,就会有问题。
问:现在做许多事都要去跑,比如申报项目、评奖,都叫“跑项目”、“跑奖”,古人很聪明,造了个“跑”字,好像是让人要带着“包”用“足”去跑。你对此类事情有什么看法?
答:世界上许多事情都是这样的。就像考试分数一样,有些东西只是一些标志而已,并不是目的,但又不能一概否定。一件事做了,但并不一定会达到预想的结果。比如高考制度,虽然自身有很多问题,有偶然性,有押题的,有些判题的人本身就误人子弟,这些问题都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就像奥运会一样,奥运会的有些运动项目的规则不见得完全合理,存在有可能做假的东西,包括兴奋剂,但是不举行奥运会连标准都没有了,就更没意思了。高考也是一样,不高考就更失去了规则,会更不好。
问:“聪明反被聪明误”这是一种规律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律?你对“聪明”有何评论?
答:这可分为几种情况,一个是“小聪明”,没有大的才智,在各种事情上总是想占些小便宜,这种人肯定成不了大事。还有另一种“聪明反被聪明误”,证明了整个社会的不合理,就是所谓的“逆向淘汰”。本来应该是优胜劣败,但却变成了“劣胜优败”。周恩来小时候,家里挂了一副对联:“生儿但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这是苏东坡的诗,意思就是无才无能才能平安度过一生,这当然是不合理的。相反,在一个合理的社会中,有五分聪明就有可能做出五分成绩,有十分聪明就有可能做出十分成绩,这样是最理想的。我从来不提倡愚蠢,“人应该愚蠢”、“做革命的老黄牛”、“革命的傻子”,这些话起码是不全面的。难道革命就得当傻子?当一个智者不行吗?像以前的观念,特别是舞台戏中穿得好、长得漂亮说话流利的都是叛徒,这显然是没道理的。
问:人生的价值是什么?现在很多人用挣钱多少来评论人的价值,用钱作唯一标准评论人对吗?
答:这很简单,这样不对,外国也不是这样,美国是一个非常重视金钱的国家,几乎任何问题都可以用钱来解决。但即使这样也不仅仅是一个钱的问题。卡特当总统的时候比他当农场主的时候收入少得多。卡特是一个以种花生为主的大农场主,但是他还是喜欢当总统。只是总统竞选连任失败了他才离开的。又比如一个大学的教授,他对于学问有一种爱还有一种骄傲。我曾经跟一些西方国家的教授也讨论过关于挣钱的问题,他们也说很喜欢高等院校里的那种学术环境,自己有专长。其他的,比如说奥运会冠军,不见得都是跟钱联系在一块的。
问:有人说:“三个和尚没水吃”描写了中华民族的劣根性,这个说法对吗?这种现象为什么这么顽固,至今依然很严重,你怎么认识这个问题?
答:我认为这不完全是一个文化、国民性的问题。我觉得首先与中国缺少现代的法治观念、规则观念有关。外国人并不是没有矛盾,但是互相扯皮的机会不是很多,因为权限规定比较明确、清晰。第二,与客观条件有关系。在一个相对狭小的空间里,容易出现问题;在选择工作岗位方面,如果有更多择业的可能性,也许就可以避免人与人之间恶性矛盾的发生。所以不见得都是中国的国民性、民族性的问题,还有一些实际的问题。另外再有就是中国的人口太多,人多了就容易冲撞。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到一个公园里去,只有三五个人,那么人见到人就会非常亲切。如果公园挤得像百货商场那样,人与人之间免不了互相讨厌。
也说做文与做人
问:你是学者作家,其中的学者角色你是如何把握的?学者与作家两者怎样发挥互补作用?理性太强烈了不影响情感的抒发吗?
答:这个只能大概来说。个人情况不完全一样,不可能要求都一样。比方说高玉宝也是作家,他有他的价值,特别是在那个时代,能从一个文盲当了作家也是很了不起的。但是总起来说,一个作家知识多一点好还是知识少一点好,学习的多一点好还是少一点好,谁都明白,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这毕竟是“两路功”,又有区别又有联系。在今天,很难设想各种最起码的知识都没有的人能成为一个好的作家。关于理性和感性问题是这样的:理性不是制约感情,而是制约感性,搞文学创作的人更多关注的是形象的、具体的东西,它不同于批评——思想大于形象,而是形象大于思想,但这并不意味着思想地位的贬低。比如《红楼梦》就是形象大于思想,怎么分析都行。如果强调思想大于形象,思想说一大堆,形象只说可怜的一点,那就没有价值了,不如干脆写理论书了。
问:做人要实在,做文要创造,二者在思维方式上是有矛盾的,你是如何处理这种矛盾的?
答:在创作中有时候会出现癫狂式的热情,这个人人都看得见。鲁迅说过,在台上演关公,下了台,就得把妆卸了,把脸洗干净,还是一个普通人,不能回了家还提着刀,喊“拿酒来!”
问:你如何看待现代知识分子比如陈寅恪、顾准、钱钟书等人的骨气问题?
答:有很多不同的情况。一个人能够忠于自己的良知,这是非常重要的。但现在的情况和以前的情况不同。有好多人把郭沫若当成是一个没有骨气的知识分子的代表,我觉得这并不公平。我们应该历史地来看,郭沫若在重庆时,敢于直面冒犯蒋介石,拍着桌子骂蒋介石,他没有骨气敢这样做吗?他不考虑个人的安危吗?但是他在革命当中,往往对事物的看法是简单化了的。一方面是对蒋介石的极端痛恨、轻蔑,另一方面是对毛泽东的崇拜。在革命当中总是这样的,如果没有对毛泽东的崇拜,就没有中国知识分子的“革命文化”。又比如陈寅恪,有人说他是有骨气的,但实际上他有他的特殊情况。他双目失明,又是一位很特殊的学者,如果他眼睛看得清清楚楚,未必敢那么说。而且他又必须看到,这并非偶然。1949年以后,大量的知识分子,愿意学习马列主义,愿意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思考问题,建立自己的新生活,但不能说这些人都没有骨气。当然也有一些人为制造出来一些带有神话色彩的东西,比如还是陈寅恪,我在书上看到,在他的一生当中,很多政要都去看望过他,换成别人做得到吗?谁有那种地位呢?在60年代非常困难的时期,陈寅恪都有特殊待遇。又比如沈从文,按照萧乾的回忆,他有很积极的一面,刚刚解放的时候他还要求参军,六十年代他还准备申请入党,现在都不提了,只说他是一个“伟大的孤独者”。有的时候人们喜欢制造神话。顾准也有他很真实的一面,文革的时候做检讨,他就要把他不好的东西都否定掉。用那种“泛道德”的观点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的“名节”的观点来评论一个人,而不考虑他的全貌,未必靠得住。相反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1949年以前,中国基本上处于一个“前革命”的状态,即所谓知识分子最推崇的一种敢于斗争的阶段,表现为不合作,斗争到底,不怕牺牲。但是如果拿这种方法用在今天,就不行了。现在我们所处的阶段,革命已经成功,当然这个革命是狭义上的,所以在革命以后,人们期待现在的知识分子能够发挥更有建设性的作用,我觉得这个也不是错误的。如果现在的知识分子一个个斗得跟“乌眼鸡”似的,一定很好么?总之,我们不能用抽象的概念来衡量一切。当然有一种类型的人是被我们所厌恶的,就是历次政治运动当中的投机者、诬陷别人的人,所谓卖友求荣者,这都是被中国历史传统所不齿的。知识分子如果有这样的纪录,就是一生的污点,永远洗不清。
问: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二者是什么关系?怎么评论它们的伟大与高尚?从发展来看二者谁对后世影响更久远?
答:文化是多元的。它有好几种,比如大仲马,法国人一直不承认他是伟大的作家,最近才刚刚承认,进入了“先贤祠”。还有,中国作家张恨水,以前对他没有太高的评价,这几年才有了较高的评价。当然,在国外的情况又是另一说了。据我所了解,有的美国博士生毕业论文写的就是张恨水。至于中国那些古典名著,实际上是处于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的一个契合点上。以《红楼梦》为例,《红楼梦》是通俗的,包括几大才子书,都是属于当时的通俗文化。当时文化的正统是写诗,而小说则是非主流化的东西。当然,通俗文化中也有许多糟粕和垃圾,乃至毒物,这些东西很快会被别人遗忘。实际上精英文化里也有很多垃圾——所谓一些装腔作势的东西。他们常常以“精英”姿态自居,可是故作“精英”姿态不等于是精英文化。
编辑:系统管理员
责任编辑:系统管理员